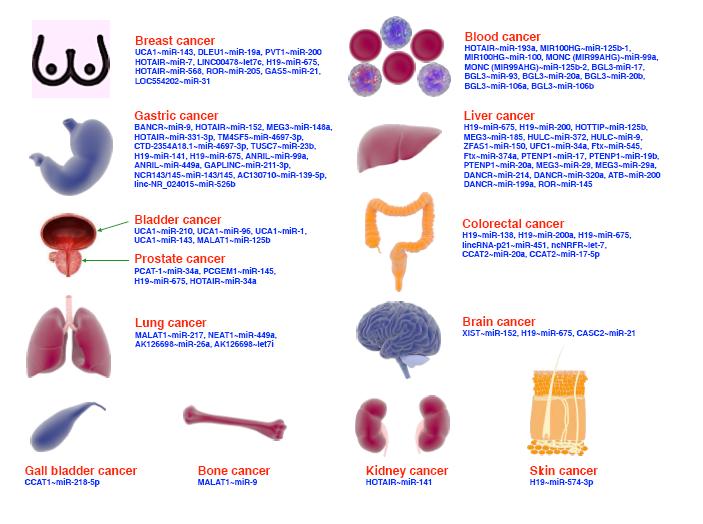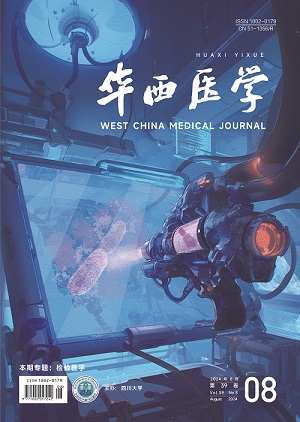引用本文: 周丹, 唐梦琳, 罗玉兰, 冯梅, 冉孟冬. 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先天畸形儿的父母焦虑与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华西医学, 2015, 30(3): 522-526. doi: 10.7507/1002-0179.20150149 复制
先天畸形是指出生时即存在的形态或结构上的异常,据国内外研究报道,先天畸形发生率约为1%~3%[1-3]。一项研究显示,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患儿中约10%为先天畸形,尽管只占有10%,但先天畸形却占有13%的NICU住院时间和26%的死亡病例[4]。而另一研究报道,先天畸形占NICU患儿的15.3%[5]。新生儿对父母有完全的依赖,如果父母存在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会影响患儿的治疗及预后[6-7]。分别针对先天畸形儿的父母和重症监护病房(ICU)新生儿父母的研究显示,其焦虑与抑郁评分均高于国内常模[6, 8-9]。ICU新生先天畸形儿的父母可能承受着更多更大的心理应激,但目前缺乏专门针对这些父母焦虑与抑郁状况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调查ICU新生先天畸形儿父母的心理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探讨心理护理和干预提供借鉴和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2013年6月1日-11月29日入住我院ICU新生先天畸形儿的父母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新生儿期发现先天性畸形的患儿的父母;② 患儿入住ICU时间>12 h;③ 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加入本研究;④ 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排除标准:① 经解释后不能充分理解问卷内容的调查者;② 不合格的问卷。
1.2 调查问卷
包括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及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①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父母的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宗教信仰、抑郁或焦虑家族史、患儿入住ICU的时间以及孩子是否唯一等;② SAS和SDS量表:由Zung先后于1965年和1971年编制,两个量表各包含有20个条目,分1~4级评分,20个条目得分相加为粗分。其中,焦虑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为焦虑标准分,依据中国常模结果,标准分<50分为无焦虑,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抑郁严重度指数=抑郁粗分/80,抑郁严重度指数<0.50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度抑郁,≥0.70为重度抑郁[10]。
1.3 调查方法
在下午探视之后,向调查对象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取得同意后,说明整个量表的填写方法,提示其认真理解每条问题的涵义,独立填写。对不能理解或看不懂问卷内容的,给予逐条解释,然后让其独立地完成量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组间焦虑、抑郁评分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间焦虑、抑郁程度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结果的累积优势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52份,有效回收率95.0%。包含152名父母,其中男88名(57.9%),女64名(42.1%);年龄19~44岁,平均29.8岁。患儿102例,其疾病构成:消化系统畸形81例(79.4%),神经系统畸形5例(4.9%),畸胎瘤3例(2.9%),先天性膈疝3例(2.9%),先天性心脏病6例(5.9%),其他4例(3.9%)。
2.1 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情况
SAS粗分为21~63分,平均(39.45±8.53)分,64名(42.1%)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33名(21.7%)为轻度焦虑,23名(15.1%)为中度焦虑,8名(5.3%)为重度焦虑。SDS粗分为20~72分,平均(43.28±10.76)分,92名(60.5%)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39名(25.7%)为轻度抑郁,30名(19.7%)为中度抑郁,23名(15.1%)为重度抑郁。
2.2 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2.2.1 各种因素对焦虑、抑郁评分的影响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调查者较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2 000元/月、无家族史的父母拥有更高的焦虑评分(P<0.05);汉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调查者较非汉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无家族史的父母拥有更高的抑郁评分(P<0.05)。见表 1。
2.2.2 各因素对焦虑、抑郁程度的影响
焦虑的严重程度受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响(P<0.05);父母的焦虑状况与孩子的性别、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别、民族、年龄、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况等因素无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的严重程度受民族、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响(P<0.05)。父母的抑郁状况与孩子的性别、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别、居住地、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况等因素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患儿父母焦虑、抑郁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以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焦虑程度、抑郁程度为应变量,分别对焦虑程度、抑郁程度进行单因素累积优势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者放入多因素回归模型中,以α=0.05为检验水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发生焦虑严重1个或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是农村的0.405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无家族史的3.180倍。少数民族的父母发生抑郁严重1个或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是汉族的0.276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无家族史的3.294倍,家庭收入每提高1个等级,患儿父母发生抑郁严重1个或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平均降低43.1%。见表 3、4。
3 讨论
先天畸形发生率较高,这部分患儿父母的焦虑与抑郁状况应受到关注。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2.1%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60.5%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焦虑评分[(39.45±8.53)分]、抑郁评分[(43.28±10.76)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焦虑(29.78±10.07)分、抑郁(33.46±8.55)分][6],与前人研究NICU患儿父母焦虑[(37.90±5.54)分]与抑郁[(40.95±8.38)分]的结果[6]相比也明显更高。当满怀欣喜迎接新生命诞生的父母不仅要面对孩子先天畸形这一事实,更加不幸的是这些孩子还需重症监护相关治疗以及存在较高的死亡风险,在这些强烈心理应激的作用下,他们的心理状况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更易出现焦虑、抑郁。
单因素分析发现,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容易发生焦虑,其程度更重,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11-12],但与张子明等[9]的调查结果不同。文化程度对不同人群的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尚存争议。本次调查人群中,文化程度低可能对先天畸形缺乏正确的认识,心理应对相对不足。所以医务人员可以利用探视时间对患儿父母进行健康宣教,多与其沟通疾病治疗及预后,提升他们对疾病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应该如此。
家庭收入是患儿父母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对焦虑评分也有一定影响。目前ICU的医疗费用较高,而新生儿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大部分医疗费用需要自己支付,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有的家庭甚至难以承受。高治疗费用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心理应激,可能会增加家庭收入低的父母出现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当详细向家属告知治疗方案、预后及费用,使其对治疗有充分的认识,在经济上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尽量呼吁社会的力量,让更多人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新生儿医疗保险制度,以减少其经济负担。
家庭居住地作为焦虑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对抑郁的严重程度也有一定影响。这与张子明等[9]NICU住院患儿家属焦虑情绪的调查结果相似。本次调查结果中居住地与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居住在农村的父母,49.4%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43.7%的家庭收入≤2 000元/月;而居住在城市的父母,仅9.2%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的为18.5%。由此可见,对居住在农村地区、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收入较差父母应额外关注他们的焦虑心理。
家族史在本次调查中对焦虑和抑郁都有显著影响,与国内肖融等[13]的调查结果和国外Tenev等[14]的Meta分析结果相似。这可能与遗传、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关。Roy等[15]对双生子的研究发现,遗传是广泛性焦虑与重症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民族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心理状态的因素,尽管在针对不同人群研究中结果并不一致[16-18],本次调查中发现汉族父母的抑郁心理状态较少数民族的父母显著。
父母的心理障碍不仅影响着他们自己健康,也与患儿的治疗及预后有着密切关系[8]。本项研究对于我们以后的医疗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医护人员应了解并重视父母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患儿父母的不良情绪,并给予关心以及心理疏导,特别是给予那些具有危险因素的父母更多关注。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重要,了解家属的心理状况,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利于医疗救治的顺利进行。同时这也体现了“以健康为中心”的护理理念。
先天畸形是指出生时即存在的形态或结构上的异常,据国内外研究报道,先天畸形发生率约为1%~3%[1-3]。一项研究显示,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患儿中约10%为先天畸形,尽管只占有10%,但先天畸形却占有13%的NICU住院时间和26%的死亡病例[4]。而另一研究报道,先天畸形占NICU患儿的15.3%[5]。新生儿对父母有完全的依赖,如果父母存在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同时也会影响患儿的治疗及预后[6-7]。分别针对先天畸形儿的父母和重症监护病房(ICU)新生儿父母的研究显示,其焦虑与抑郁评分均高于国内常模[6, 8-9]。ICU新生先天畸形儿的父母可能承受着更多更大的心理应激,但目前缺乏专门针对这些父母焦虑与抑郁状况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调查ICU新生先天畸形儿父母的心理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探讨心理护理和干预提供借鉴和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2013年6月1日-11月29日入住我院ICU新生先天畸形儿的父母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新生儿期发现先天性畸形的患儿的父母;② 患儿入住ICU时间>12 h;③ 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加入本研究;④ 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排除标准:① 经解释后不能充分理解问卷内容的调查者;② 不合格的问卷。
1.2 调查问卷
包括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及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①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父母的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宗教信仰、抑郁或焦虑家族史、患儿入住ICU的时间以及孩子是否唯一等;② SAS和SDS量表:由Zung先后于1965年和1971年编制,两个量表各包含有20个条目,分1~4级评分,20个条目得分相加为粗分。其中,焦虑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为焦虑标准分,依据中国常模结果,标准分<50分为无焦虑,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抑郁严重度指数=抑郁粗分/80,抑郁严重度指数<0.50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度抑郁,≥0.70为重度抑郁[10]。
1.3 调查方法
在下午探视之后,向调查对象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取得同意后,说明整个量表的填写方法,提示其认真理解每条问题的涵义,独立填写。对不能理解或看不懂问卷内容的,给予逐条解释,然后让其独立地完成量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组间焦虑、抑郁评分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间焦虑、抑郁程度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结果的累积优势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52份,有效回收率95.0%。包含152名父母,其中男88名(57.9%),女64名(42.1%);年龄19~44岁,平均29.8岁。患儿102例,其疾病构成:消化系统畸形81例(79.4%),神经系统畸形5例(4.9%),畸胎瘤3例(2.9%),先天性膈疝3例(2.9%),先天性心脏病6例(5.9%),其他4例(3.9%)。
2.1 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情况
SAS粗分为21~63分,平均(39.45±8.53)分,64名(42.1%)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33名(21.7%)为轻度焦虑,23名(15.1%)为中度焦虑,8名(5.3%)为重度焦虑。SDS粗分为20~72分,平均(43.28±10.76)分,92名(60.5%)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39名(25.7%)为轻度抑郁,30名(19.7%)为中度抑郁,23名(15.1%)为重度抑郁。
2.2 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2.2.1 各种因素对焦虑、抑郁评分的影响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调查者较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2 000元/月、无家族史的父母拥有更高的焦虑评分(P<0.05);汉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调查者较非汉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无家族史的父母拥有更高的抑郁评分(P<0.05)。见表 1。
2.2.2 各因素对焦虑、抑郁程度的影响
焦虑的严重程度受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响(P<0.05);父母的焦虑状况与孩子的性别、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别、民族、年龄、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况等因素无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的严重程度受民族、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响(P<0.05)。父母的抑郁状况与孩子的性别、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别、居住地、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况等因素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患儿父母焦虑、抑郁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以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焦虑程度、抑郁程度为应变量,分别对焦虑程度、抑郁程度进行单因素累积优势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者放入多因素回归模型中,以α=0.05为检验水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发生焦虑严重1个或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是农村的0.405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无家族史的3.180倍。少数民族的父母发生抑郁严重1个或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是汉族的0.276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无家族史的3.294倍,家庭收入每提高1个等级,患儿父母发生抑郁严重1个或以上等级的可能性平均降低43.1%。见表 3、4。
3 讨论
先天畸形发生率较高,这部分患儿父母的焦虑与抑郁状况应受到关注。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2.1%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60.5%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焦虑评分[(39.45±8.53)分]、抑郁评分[(43.28±10.76)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焦虑(29.78±10.07)分、抑郁(33.46±8.55)分][6],与前人研究NICU患儿父母焦虑[(37.90±5.54)分]与抑郁[(40.95±8.38)分]的结果[6]相比也明显更高。当满怀欣喜迎接新生命诞生的父母不仅要面对孩子先天畸形这一事实,更加不幸的是这些孩子还需重症监护相关治疗以及存在较高的死亡风险,在这些强烈心理应激的作用下,他们的心理状况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更易出现焦虑、抑郁。
单因素分析发现,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容易发生焦虑,其程度更重,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11-12],但与张子明等[9]的调查结果不同。文化程度对不同人群的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尚存争议。本次调查人群中,文化程度低可能对先天畸形缺乏正确的认识,心理应对相对不足。所以医务人员可以利用探视时间对患儿父母进行健康宣教,多与其沟通疾病治疗及预后,提升他们对疾病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应该如此。
家庭收入是患儿父母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对焦虑评分也有一定影响。目前ICU的医疗费用较高,而新生儿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大部分医疗费用需要自己支付,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有的家庭甚至难以承受。高治疗费用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心理应激,可能会增加家庭收入低的父母出现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当详细向家属告知治疗方案、预后及费用,使其对治疗有充分的认识,在经济上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尽量呼吁社会的力量,让更多人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新生儿医疗保险制度,以减少其经济负担。
家庭居住地作为焦虑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对抑郁的严重程度也有一定影响。这与张子明等[9]NICU住院患儿家属焦虑情绪的调查结果相似。本次调查结果中居住地与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居住在农村的父母,49.4%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43.7%的家庭收入≤2 000元/月;而居住在城市的父母,仅9.2%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的为18.5%。由此可见,对居住在农村地区、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收入较差父母应额外关注他们的焦虑心理。
家族史在本次调查中对焦虑和抑郁都有显著影响,与国内肖融等[13]的调查结果和国外Tenev等[14]的Meta分析结果相似。这可能与遗传、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关。Roy等[15]对双生子的研究发现,遗传是广泛性焦虑与重症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民族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心理状态的因素,尽管在针对不同人群研究中结果并不一致[16-18],本次调查中发现汉族父母的抑郁心理状态较少数民族的父母显著。
父母的心理障碍不仅影响着他们自己健康,也与患儿的治疗及预后有着密切关系[8]。本项研究对于我们以后的医疗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医护人员应了解并重视父母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患儿父母的不良情绪,并给予关心以及心理疏导,特别是给予那些具有危险因素的父母更多关注。面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重要,了解家属的心理状况,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利于医疗救治的顺利进行。同时这也体现了“以健康为中心”的护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