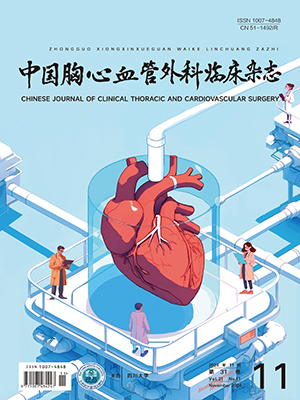引用本文: 贺彦, 刘迎龙, 苏俊武, 程沛, 陈焱.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术后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分析.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6, 23(2): 147-150. doi: 10.7507/1007-4848.20160033 复制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是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解剖改变为四支肺静脉回流至右心系统,1岁以内自然生存率25%,需要婴儿期尽早手术[1-2]。这类患儿畸形复杂,多数年龄小、体重低,术前左心系统发育差,肺静脉淤血。虽然近10年来疗效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机械通气支持心肺功能[3-5]。为指导临床准确选择拔管时机,期望进一步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我们分析了此类患儿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回顾性分析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诊断为TAPVC行根治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死亡病例。定义大于平均机械通气时间的患儿为延迟拔管组。比较延迟拔管组和正常拔管组患儿的年龄、体重、诊断分型、术前超声左心室大小、术前是否肺静脉梗阻、房水平交通大小、体外循环时间、升主动脉阻断时间、术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ISO)、左心房压(LAP)、术后超声左心室大小、肺静脉最大流速。术前诊断常规应用超声心动检查,对于肺静脉观察不清的病例,特别是混合型TAPVC,行胸部心脏大血管CT检查。
1.2 手术方法
将肺静脉引流至左心系统,同时矫正其他心内畸形,包括房间隔缺损,是各型TAPVC的手术目的。心上型,将肺静脉共干与左心房后壁或房顶吻合,游离结扎垂直静脉。心内型,扩大房间隔缺损或未闭卵圆孔至冠状静脉窦或肺静脉入右房处,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将肺静脉隔至左心房。心下型,手术方式大致同心上型。混合型,根据不同的心脏解剖形态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1.3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全组共97例,男55例(56.7%)、女42例,中位数年龄4.4(2,12)个月,中位数体重6(4.6,7.85)kg。心上型55例(56.7%),心内型31例(32.0%),心下型4例(4.1%),混合型7例(7.2%)。术前超声左室舒期末内径(18.66±6.49)mm,肺静脉梗阻(肺静脉流速≥2 m/s)18例(18.6%),房水平分流(10.26±6.47)mm。全组体外循环时间(99.37±37.29)min,升主动脉阻断时间(54.1±21.0)min。术后ISO评分(13.54±6.31)分,LAP(9.39±2.9)mm Hg。术后超声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21(18.5,25.0)mm,肺静脉流速(98.67±46.77)m/s。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中位数49(25,90)h,住ICU时间6(4,10)d。
延迟拔管组50例(51.5%),与正常拔管组(47例)比较,延迟拔管的单因素变量有:年龄、体重、术前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房间隔交通大小、术后ISO评分、术后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P < 0.01)及体外循环时间(P < 0.05),见表 1。Logistic回归后退法显示,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是:年龄(OR=0.804,95%CI 0.71,0.91)和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OR=1.016,95%CI 1.003,1.029),见表 2。
3 讨论
TAPVC是出生后需要早期手术的紫绀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其解剖及围术期病理生理特点使患儿术后需要较长时间的呼吸机支持。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监护室所有患儿术后平均呼吸机时间为20.17 h,ICU住院时间为2.97 d;而TAPVC术后呼吸机支持中位时间为49 h,住ICU中位时间为6 d,且有51.5%的患儿机械通气和住ICU时间大大超过该时间。
通常认为,超声测量肺静脉最大血流速度 > 120 cm/s时,诊断为肺静脉狭窄。肺静脉流速为120~140 cm/s为轻度狭窄,术后不需外科特殊处理;流速 > 160 cm/s为重度狭窄,影响预后;流速≥200 cm/s,诊断为肺静脉梗阻,术后发生率大约为9%~18%,是TAPVC术后严重并发症之一[6-9]。本研究显示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是影响拔管的危险因素。延迟拔管组平均肺静脉流速为(115.7±50.16)cm/s,而正常拔管组流速仅为(80.55±35.14)cm/s。术后肺静脉流速越快的患儿,肺静脉淤血的程度越严重,对正压机械通气支持的需求时间越长。目前广泛认同的减少术后肺静脉狭窄的方法包括心上路径改良吻合及无内膜接触缝合技术(Sutureless)等[10-13]。
本研究中患儿手术前后的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房间交通大小及术后ISO评分是影响拔管的单因素变量。TAPVC患儿术前肺血回流右心房,通过房间隔交通,再回流左心房。术前房间隔交通小、左心室充盈欠佳者,术后肺血直接回流左心房,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会逐渐增大,在此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血管活性药物支持。正压机械通气帮助患儿减少呼吸功,降低心脏负担;同时呼气末正压对肺水肿患儿心脏功能也有一定的帮助[14]。因此手术前后左心室小、房间隔交通小及术后需要较大血管活性药物支持的患儿,同样需要更长时间的呼吸支持。
本研究中年龄、体重和体外循环时间是影响拔管的单因素变量。体外循环增加患儿体内炎性因子释放,造成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减少,间质渗出增加,降低换气功能;开胸手术操作可能直接损伤肺组织,破坏胸膜的完整性,影响通气功能[15]。与晶体预充相比,体外循环胶体预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术后心肌水肿[16],但手术操作对心肌的损伤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体外循环开胸手术对患儿的呼吸循环功能有很大影响。年龄越小,患儿心肺功能发育越不完善,代偿能力越差,体外循环的影响越大,术后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时间越长。Karamlous[17]和James等[18]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年龄小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
既往研究显示,术前的肺静脉梗阻情况也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19]。但也有学者提出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因肺静脉梗阻导致的急诊手术已经不再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20]。本研究术前的肺静脉梗阻并未影响术后呼吸机时间,考虑因素如下:(1)手术技术成熟,虽然术前有肺静脉梗阻,但手术对梗阻解除完善,使得该因素不成为影响拔管的关键,只有术后肺静脉流速作为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2)术前梗阻严重者,手术不能完整进行,术后患儿死亡,这类患儿被排除在外。(3)统计处理时,“术前肺静脉是否梗阻”和“是否延迟拔管”均作为计数资料,可能忽略了肺静脉流速和拔管时间之间的相关性。如继续扩大样本量,可能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心,患儿年龄和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是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而患儿体重、围术期左心室内径、房间隔交通大小、体外循环时间及术后ISO评分是影响拔管的单因素变量。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是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解剖改变为四支肺静脉回流至右心系统,1岁以内自然生存率25%,需要婴儿期尽早手术[1-2]。这类患儿畸形复杂,多数年龄小、体重低,术前左心系统发育差,肺静脉淤血。虽然近10年来疗效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机械通气支持心肺功能[3-5]。为指导临床准确选择拔管时机,期望进一步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我们分析了此类患儿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回顾性分析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诊断为TAPVC行根治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死亡病例。定义大于平均机械通气时间的患儿为延迟拔管组。比较延迟拔管组和正常拔管组患儿的年龄、体重、诊断分型、术前超声左心室大小、术前是否肺静脉梗阻、房水平交通大小、体外循环时间、升主动脉阻断时间、术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ISO)、左心房压(LAP)、术后超声左心室大小、肺静脉最大流速。术前诊断常规应用超声心动检查,对于肺静脉观察不清的病例,特别是混合型TAPVC,行胸部心脏大血管CT检查。
1.2 手术方法
将肺静脉引流至左心系统,同时矫正其他心内畸形,包括房间隔缺损,是各型TAPVC的手术目的。心上型,将肺静脉共干与左心房后壁或房顶吻合,游离结扎垂直静脉。心内型,扩大房间隔缺损或未闭卵圆孔至冠状静脉窦或肺静脉入右房处,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将肺静脉隔至左心房。心下型,手术方式大致同心上型。混合型,根据不同的心脏解剖形态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1.3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全组共97例,男55例(56.7%)、女42例,中位数年龄4.4(2,12)个月,中位数体重6(4.6,7.85)kg。心上型55例(56.7%),心内型31例(32.0%),心下型4例(4.1%),混合型7例(7.2%)。术前超声左室舒期末内径(18.66±6.49)mm,肺静脉梗阻(肺静脉流速≥2 m/s)18例(18.6%),房水平分流(10.26±6.47)mm。全组体外循环时间(99.37±37.29)min,升主动脉阻断时间(54.1±21.0)min。术后ISO评分(13.54±6.31)分,LAP(9.39±2.9)mm Hg。术后超声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21(18.5,25.0)mm,肺静脉流速(98.67±46.77)m/s。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中位数49(25,90)h,住ICU时间6(4,10)d。
延迟拔管组50例(51.5%),与正常拔管组(47例)比较,延迟拔管的单因素变量有:年龄、体重、术前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房间隔交通大小、术后ISO评分、术后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P < 0.01)及体外循环时间(P < 0.05),见表 1。Logistic回归后退法显示,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是:年龄(OR=0.804,95%CI 0.71,0.91)和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OR=1.016,95%CI 1.003,1.029),见表 2。
3 讨论
TAPVC是出生后需要早期手术的紫绀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其解剖及围术期病理生理特点使患儿术后需要较长时间的呼吸机支持。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监护室所有患儿术后平均呼吸机时间为20.17 h,ICU住院时间为2.97 d;而TAPVC术后呼吸机支持中位时间为49 h,住ICU中位时间为6 d,且有51.5%的患儿机械通气和住ICU时间大大超过该时间。
通常认为,超声测量肺静脉最大血流速度 > 120 cm/s时,诊断为肺静脉狭窄。肺静脉流速为120~140 cm/s为轻度狭窄,术后不需外科特殊处理;流速 > 160 cm/s为重度狭窄,影响预后;流速≥200 cm/s,诊断为肺静脉梗阻,术后发生率大约为9%~18%,是TAPVC术后严重并发症之一[6-9]。本研究显示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是影响拔管的危险因素。延迟拔管组平均肺静脉流速为(115.7±50.16)cm/s,而正常拔管组流速仅为(80.55±35.14)cm/s。术后肺静脉流速越快的患儿,肺静脉淤血的程度越严重,对正压机械通气支持的需求时间越长。目前广泛认同的减少术后肺静脉狭窄的方法包括心上路径改良吻合及无内膜接触缝合技术(Sutureless)等[10-13]。
本研究中患儿手术前后的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房间交通大小及术后ISO评分是影响拔管的单因素变量。TAPVC患儿术前肺血回流右心房,通过房间隔交通,再回流左心房。术前房间隔交通小、左心室充盈欠佳者,术后肺血直接回流左心房,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会逐渐增大,在此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血管活性药物支持。正压机械通气帮助患儿减少呼吸功,降低心脏负担;同时呼气末正压对肺水肿患儿心脏功能也有一定的帮助[14]。因此手术前后左心室小、房间隔交通小及术后需要较大血管活性药物支持的患儿,同样需要更长时间的呼吸支持。
本研究中年龄、体重和体外循环时间是影响拔管的单因素变量。体外循环增加患儿体内炎性因子释放,造成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减少,间质渗出增加,降低换气功能;开胸手术操作可能直接损伤肺组织,破坏胸膜的完整性,影响通气功能[15]。与晶体预充相比,体外循环胶体预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术后心肌水肿[16],但手术操作对心肌的损伤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体外循环开胸手术对患儿的呼吸循环功能有很大影响。年龄越小,患儿心肺功能发育越不完善,代偿能力越差,体外循环的影响越大,术后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时间越长。Karamlous[17]和James等[18]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年龄小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
既往研究显示,术前的肺静脉梗阻情况也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19]。但也有学者提出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因肺静脉梗阻导致的急诊手术已经不再是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20]。本研究术前的肺静脉梗阻并未影响术后呼吸机时间,考虑因素如下:(1)手术技术成熟,虽然术前有肺静脉梗阻,但手术对梗阻解除完善,使得该因素不成为影响拔管的关键,只有术后肺静脉流速作为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2)术前梗阻严重者,手术不能完整进行,术后患儿死亡,这类患儿被排除在外。(3)统计处理时,“术前肺静脉是否梗阻”和“是否延迟拔管”均作为计数资料,可能忽略了肺静脉流速和拔管时间之间的相关性。如继续扩大样本量,可能会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心,患儿年龄和术后肺静脉最大流速是延迟拔管的危险因素。而患儿体重、围术期左心室内径、房间隔交通大小、体外循环时间及术后ISO评分是影响拔管的单因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