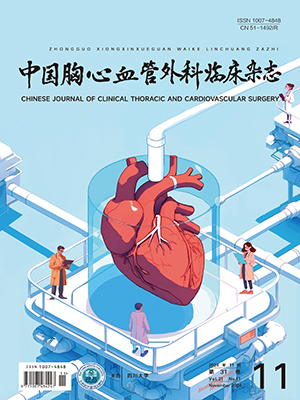引用本文: 高珂, 赖玉田, 黄健, 王一帆, 王晓玮, 车国卫.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前肺康复训练前后血清肺表面活性蛋白 D(SP-D)改变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相关性的随机对照试验.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7, 24(5): 330-337. doi: 10.7507/1007-4848.201701003 复制
肺癌是全球男性和发达国家女性因癌症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种类[1],手术仍然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是手术后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在围手术期进行心肺康复评估及肺康复治疗能有效预防及改善术后患者心肺并发症、提高患者肺功能、运动耐力,改善术后生活质量[3],而肺表面活性蛋白 D(surfactant protein D,SP-D)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肺功能的变化。因此,我们对连续收治的可手术的肺癌合并高危因素患者,通过手术前高危因素筛查,选择至少有一个危险因素的患者随机分组,研究术前肺康复训练患者围手术期不同时间点血清 SP-D 浓度的变化及其与手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纳入2015 年 3~12 月华西医院胸外科连续收治拟手术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192 例,术前均根据中国肺癌诊疗指南(2015 版)的规定进行常规检查,无手术禁忌证。
纳入标准:(1)至少有一个手术并发症的危险因素;(2)根据中国肺癌诊疗指南病理学诊断为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或临床及影像学高度怀疑肺癌拟行手术;(3)符合中国肺癌诊疗指南中规定的施行胸腔镜或开胸单肺叶切除手术+系统淋巴结清扫术;(4)同意术前根据试验要求进行检查,发现高危患者愿意接受术前肺康复训练计划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或术后石蜡病理检查证实不符合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诊断;(2)术中发现需要行全肺切除、联合肺叶切除和需要行肺动脉和支气管袖式成形肺叶切除术;(3)术中出血量超过 1 000 ml 和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中转开胸或者术后需要再次手术止血;(4)试验期间拒绝继续按照试验计划进行肺康复训练或检测;(5)在标本检测时发现标本不合格的(标本污染,标本量少不足以完成所有指标检测)。
根据患者病史、静态肺功能和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评估心肺功能,评估术前存在的并发症高危因素,其中至少有一项高危因素[4]的患者共 80 例随机分成两组(康复组和对照组,用计算机产生随机序列号,将序列号装入不透光的密封信封里)。临床资料收集和分析分两组进行,对医师和统计分析师实施盲法。
1.2 方法
1.2.1 基础肺功能检测指标 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肺功能室完成并出具实验报告。测定和评估肺通气功能(肺容积、肺通气量、小气道功能、呼吸动力学、吸入气体分布、呼吸肌功能)和肺换气功能(弥散功能、通气血流比值)。
1.2.2 心肺运动试验方法检测及项目 阻力均为 27 瓦,要求 6 min 之内尽可能快速地运动,如果患者感觉累或气促可以减慢速度或者停止运动,恢复后继续运动;检测项目包括从患者静息开始检测心律和血氧饱和度到运动结束停止检测,Borg 呼吸困难评分,患者 6 分钟运动距离(6 minute walk distance,6-MWD)和能量消耗。
1.2.3 围手术期肺癌患者肺康复评估及训练方案 2.0(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
1.2.3.1 肺癌患者合并高危因素及评估标准 (1)年龄≥75 岁和吸烟量≥400 年支 评价标准:高龄,年龄≥75 岁(男性若合并吸烟则年龄>60 岁,女性年龄>70 岁);长期大量吸烟,吸烟史≥400 年支[5]。
(2)气管定植菌 评价标准:入院时经纤维支气管镜取呼吸道细菌学标本,以防污染样本毛刷≥103 cfu/ml、支气管肺泡灌洗液≥104 cfu/ml 确定为细菌定植标准[5]。
(3)气道高反应性(airway high response,AHR) 评价标准(以下 3 条满足其中一条即诊断):① CPET 检测过程中,若肺部出现干鸣音或血氧饱和度降低大于 15%,则诊断为气道高反应性;② 若不能进行 CPET,也可在爬楼梯训练过程中(33 台阶),速度为每秒钟一个台阶,若肺部出现干鸣音或血氧饱和度降低大于 15%,也可粗略诊断为气道高反应性;③ 支气管舒张试验[4]。
(4)呼气峰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PFE) PF<250 L/min 评价标准:应用峰流速仪或哮喘检测仪发现的高危因素,PEF<250 L/min[6]。
(5)肺功能处于临界状态(marginal pulmonary function) 评价标准: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1.0 L 或一秒率(FEV1/FVC)<50%[7]。
1.2.3.2 肺康复训练方案 (1)抗感染:根据标准应用;(2)祛痰:术前 3~7 d 及术后 3~7 d; 沐舒坦 30 mg,ivgtt,Q8h 和/或吉诺通 300 mg,tid po(必需);(3)平喘或消炎:术前 3~7 d、术后 3~7 d;普米克令舒+博利康尼,4 ml+2 ml/time,2 time/d(必需);(4)激励式肺量计吸气训练:(VOLDYNE5000)患者取易于深吸气的体位,一手握住激励式肺量计,用嘴含住咬嘴并确保密闭不漏气,然后进行深慢的吸气,将黄色的浮标吸升至预设的标记点,然后屏气 2~3 s,移开咬嘴呼气。重复以上步骤,每组进行 6~10 次训练,然后休息。在非睡眠时间,每 2 h 重复一组训练,以不引起患者疲劳为宜。3~7 d(必需);(5)功率自行车运动训练:患者自行调控速度,在承受范围内逐步加快步行速度及自行车功率。运动量控制在呼吸困难指数(Borg)评分 5~7 分,若在运动过程中有明显气促、腿疲倦、血氧饱和度下降(<88%)或其它合并疾病引起身体不适则休息,待恢复原状后再继续进行训练。每次约 15~20 min,每天 2 次,疗程为 7~14 d(可选)。(6)登楼梯训练:在专业治疗师陪同下进行,在运动过程中调整呼吸节奏,采用缩唇呼吸,用力时呼气,避免闭气,稍感气促时可坚持进行,若有明显呼吸困难,则短暂休息,尽快继续运动。每次约 15~30 min,每天 2 次,疗程 3~7 d(可选)。
1.2.4 肺部并发症分类及评价标准 (1)PPC 包括肺部感染、肺栓塞、乳糜胸、皮下气肿、咯血、声音嘶哑、支气管胸膜瘘、手术后持续肺漏气、手术后胸腔积液(中到大量)和积气(肺压缩≥30%)、肺不张、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呼吸衰竭(肺部并发症分类及评价标准见表 1)。(2)肺部感染的标准:含有以下指标 3 个或以上为手术后肺炎[8-9]:① 手术后 72 h 发热,体温>38℃;或 72 h 以内体温再度升高。② 白细胞计数升高(>12~15×109/L)或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值以后的再升高,超过 10×109/L。③ 胸部影像学提示肺组织实变或不断增加的斑片状阴影。④ 咳出脓性痰液或痰培养阳性。其中如果包含 ④,仅需要其他一项即可视为手术后肺炎(postoperative pneumonia,POP)或经呼吸科会诊确定为肺部感染,并需要更换抗生素或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
1.2.5 手术方法 胸腔镜肺叶切除患者手术方法:单向式胸腔镜肺叶切除法+系统淋巴结清扫[10]。开胸患者应用常规后外侧切口,肺叶切除术+系统淋巴结清扫。系统淋巴结清扫左侧必须清扫第 5、6、7、8、9、10 组淋巴结,右侧包括第 2、3、4、7、8、9、10 组淋巴结。
1.2.6 术后处理方法 术后疼痛处理均应用镇痛泵(盐酸曲马多注射液,1~1.5 mg/h),均早期促使患者下床活动。必要时应用非甾体类止痛药(氨酚羟考酮片或布洛芬缓释胶囊)。镇痛泵于胸腔引流管拔除的同时也一起停止。两组患者均根据胸腔引流气体和液体量决定行胸部 X 线片检查时间,并根据胸部 X 线片结果决定是否拔除胸腔引流管。
1.3 血浆中 SP-D 浓度的测定
在患者入院当天、手术前 1 d、手术后第 1 d、手术后第 3 d 及出院前 1 d 5 个时间点,分别采集患者外周血 5 ml,待血液自然凝固 10~20 min,离心 20 min,2 000 转/分,收集血清,应用双抗体夹心法测定标本中SP-D水平。试验流程图见图 1。SP-D ELISA 试剂盒由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图1
试验流程图
图1
试验流程图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描述,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的t 检验或方差分析;样本在作t 检验和方差分析前均先作正态分析或方差齐性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使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生理学特征分析
患者流程见图 2,其中康复组 36 例 [男 25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63.98±8.32)岁],对照组 44 例 [男 32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64.58±6.71)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的病理类型、病理分期、手术方式、合并症(COPD/高血压/糖尿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康复组发生 PPC2 例(2/36,5.56%)。两组 PPC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对照组 PPC 发生率更高(10/44,22.73%);见表 2。
 图2
80 例患者随机分组流程图
图2
80 例患者随机分组流程图
2.2 两组患者高危因素及术后并发症种类分布
康复组患者 36 例,共检出高危因素 63 项,其中有 1 项高危因素患者 15 例,2 项 16 例,3 项 4 例,3 项以上 1 例;对照组患者 44 例,共检出高危因素 74 项,其中有 1 项高危因素的患者 20 例,2 项 19 例,3 项 4 例,3 项以上 1 例。两组患者术前高危因素的构成比和高危因素负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康复组发生术后并发症的患者 2 例(共 3 类并发症),对照组发生术后并发症的患者 10 例(共 15 类并发症)。并发症种类分布见表 3。
2.3 两组患者在围手术期血清 SP-D 水平变化分析
康复训练前(入院时)血清 SP-D 水平在康复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75±5.57)ng/mlvs. (31.16±7.81)ng/ml ,P=0.872],康复训练后(手术前 1 d)血清 SP-D 水平在康复组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22±3.08)ng/mlvs. (30.29±5.80)ng/ml ,P=0.000];而手术后第 1、2 天及出院时血清 SP-D 水平在康复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4,图 3a)。
 图3
患者不同指标分组围手术期血清 SP-D 水平变化的比较 a. 80 例患者按照康复/对照组分组,比较两组血清 SP-D 的变化; b. 80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c. 未行肺康复训练的 44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d. 36 例肺康复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图3
患者不同指标分组围手术期血清 SP-D 水平变化的比较 a. 80 例患者按照康复/对照组分组,比较两组血清 SP-D 的变化; b. 80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c. 未行肺康复训练的 44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d. 36 例肺康复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2.4 80 例高危因素患者围手术期的血清 SP-D 水平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相关性
80 例肺癌合并高危因素患者按照术后是否发生 PPC,分成 PPC 组(n=12)和非 PPC 组(n=68)。PPC 组患者血清 SP-D 水平在手术前 1 d 的血清 SP-D 水平高于非 PP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1.18±5.43)ng/mlvs. (26.66±4.97)ng/ml ,P=0.005,表 5,图 3b]。
2.5 术前对照组患者血清 SP-D 水平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相关性分析
对照组患者术后发生 PPC10 例(22.73%,10/44),未发生 PPC34 例(34/44)。PPC 组患者术前(入院当天)血清 SP-D 水平高于非 PP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93±4.15)ng/mlvs. (29.81±7.47)ng/ml,P=0.045,表 6,图 3c]。
2.6 术前康复组肺癌患者血清 SP-D 水平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相关性分析
康复组患者术后发生 PPC 2 例(5.56%,2/36),未发生 PPC 34 例(34/36)。PPC 组患者术前(入院当天和术前 1 d)血清 SP-D 水平变化幅度[(29.78±2.52)ng/mlvs. (27.84±3.05)ng/ml]低于非 PP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80±5.48)ng/mlvs. (24.18±3.12)ng/ml,表 7,图 3d]。
3 讨论
已有研究证实[7,11],围手术期肺康复训练可以改善患者心肺状态,减低 PPC 发生率。如何解释肺康复训练降低 PPC 发生率的机制,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12-14]。目前相对一致的结果是肺康复训练可以改善患者运动耐力(6 分钟步行距离、疲劳指数)和呼吸困难指数[15-16],而呼吸功能各项指标在肺康复前后的变化则有较大争议[7,17-18]。
不同于常规临床病史和生理学参数,生物标志物在不同的层面揭示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可以连同临床观察指标一起更好地解释临床现象的原因。Paone 等[19]报道了使用无创通气治疗 COPD 的长期效果,发现干预手段可以导致血清炎症因子的变化。Morano 等[20]首次采用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比较了肺康复对血清纤维蛋白原水平的影响,结果提示对于等待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前肺康复可以降低血清纤维蛋白原的水平,提高运动耐力指标,改善生活质量。纤维蛋白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炎症因子,与 COPD 和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相关,但其是下游反应产物,由多部位分泌,特异性较差[21-22]。由靶器官分泌的特异性蛋白特异性更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Jehn 等[23]应用血清前心房利钠肽和肾上腺髓质激素水平预测稳定期 COPD 患者发生心脏事件的风险,开创了原因靶器官蛋白作为生物标志物预测疾病发生的先河。SP-D 也被用于预测 COPD 恶化的风险[24]。SP-D 是由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分泌的一类糖蛋白,与肺内的天然免疫有关,在肺泡通透性增加的情况下会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从而得以在外周血液中检测到[25]。我们的研究首次引入血清 SP-D 研究肺康复训练对其血清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康复组患者手术前 1 d(康复后)的血清 SP-D 水平下降幅度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提示术前肺康复训练可以降低肺癌手术患者血清 SP-D 水平,SP-D 在康复前后的变化与手术后 PPC 的发生相关联。
SP-D 是水溶性蛋白,除参与肺泡张力的维持外,还与机体和肺的免疫功能和炎症调节相关,参与了肺的免疫调节及病原体的吞噬及凋亡机制[26],外源性因素可以影响肺组织 SP-D 的表达水平[27],在肺康复前后血清 SP-D 水平的变化可以间接反映肺康复训练对肺功能各项指标的变化。结合目前对于肺康复是否改善肺呼吸功能指标的争论,我们认为肺康复训练不仅改善了肺的呼吸功能,同时伴随变化的还可能有肺组织局部通透性和免疫状态。在这一点上,部分关于肺康复对其他炎症因子水平变化的研究佐证了我们的观点[28-29]。
我们的试验首次研究了血清 SP-D 水平在肺癌患者康复及手术前后的变化,结果显示:不管康复与否,肺叶切除以后血清 SP-D 水平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手术后切除肺叶,减少了 SP-D 的直接分泌有关。但其下降的比例与手术后肺组织损失比例不成正比,这可能与手术后应激、局部炎症反应、手术后药物的使用等多种因素有关。
将患者按照有无 PPC 分组,研究 PPC 与围手术期血清 SP-D 的变化关系,结果发现,全组 80 例患者(无论是否肺康复训练)按有无 PPC 分组后,并发症组患者血清 SP-D 水平在手术前 1 d 的血清 SP-D 水平显著高于无并发症组(P=0.005),提示手术前即时的血清 SP-D 水平对手术后并发症预测有一定的作用。
研究进一步将 80 例患者分层研究的结果发现:(1)未接受肺康复训练的患者 44 例按有无 PPC 分组,两组患者仅在入院当天血清 SP-D 浓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他节点之间血清 SP-D 浓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术前血清 SP-D 水平较高是 PPC 的危险因素。(2)接受肺康复训练的患者 36 例中并发症发生组患者术前(入院当天和术前 1 d)血清 SP-D 水平变化幅度显著低于非 PPC 组,提示血清 SP-D 水平可以反映肺康复的效果,并与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相关。
综上所述,术前肺康复训练可以降低肺癌合并高危因素患者术后并发症,血清 SP-D 水平变化程度可作为肺康复训练的评价指标。
肺癌是全球男性和发达国家女性因癌症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种类[1],手术仍然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是手术后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在围手术期进行心肺康复评估及肺康复治疗能有效预防及改善术后患者心肺并发症、提高患者肺功能、运动耐力,改善术后生活质量[3],而肺表面活性蛋白 D(surfactant protein D,SP-D)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肺功能的变化。因此,我们对连续收治的可手术的肺癌合并高危因素患者,通过手术前高危因素筛查,选择至少有一个危险因素的患者随机分组,研究术前肺康复训练患者围手术期不同时间点血清 SP-D 浓度的变化及其与手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纳入2015 年 3~12 月华西医院胸外科连续收治拟手术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192 例,术前均根据中国肺癌诊疗指南(2015 版)的规定进行常规检查,无手术禁忌证。
纳入标准:(1)至少有一个手术并发症的危险因素;(2)根据中国肺癌诊疗指南病理学诊断为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或临床及影像学高度怀疑肺癌拟行手术;(3)符合中国肺癌诊疗指南中规定的施行胸腔镜或开胸单肺叶切除手术+系统淋巴结清扫术;(4)同意术前根据试验要求进行检查,发现高危患者愿意接受术前肺康复训练计划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或术后石蜡病理检查证实不符合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诊断;(2)术中发现需要行全肺切除、联合肺叶切除和需要行肺动脉和支气管袖式成形肺叶切除术;(3)术中出血量超过 1 000 ml 和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中转开胸或者术后需要再次手术止血;(4)试验期间拒绝继续按照试验计划进行肺康复训练或检测;(5)在标本检测时发现标本不合格的(标本污染,标本量少不足以完成所有指标检测)。
根据患者病史、静态肺功能和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评估心肺功能,评估术前存在的并发症高危因素,其中至少有一项高危因素[4]的患者共 80 例随机分成两组(康复组和对照组,用计算机产生随机序列号,将序列号装入不透光的密封信封里)。临床资料收集和分析分两组进行,对医师和统计分析师实施盲法。
1.2 方法
1.2.1 基础肺功能检测指标 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肺功能室完成并出具实验报告。测定和评估肺通气功能(肺容积、肺通气量、小气道功能、呼吸动力学、吸入气体分布、呼吸肌功能)和肺换气功能(弥散功能、通气血流比值)。
1.2.2 心肺运动试验方法检测及项目 阻力均为 27 瓦,要求 6 min 之内尽可能快速地运动,如果患者感觉累或气促可以减慢速度或者停止运动,恢复后继续运动;检测项目包括从患者静息开始检测心律和血氧饱和度到运动结束停止检测,Borg 呼吸困难评分,患者 6 分钟运动距离(6 minute walk distance,6-MWD)和能量消耗。
1.2.3 围手术期肺癌患者肺康复评估及训练方案 2.0(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
1.2.3.1 肺癌患者合并高危因素及评估标准 (1)年龄≥75 岁和吸烟量≥400 年支 评价标准:高龄,年龄≥75 岁(男性若合并吸烟则年龄>60 岁,女性年龄>70 岁);长期大量吸烟,吸烟史≥400 年支[5]。
(2)气管定植菌 评价标准:入院时经纤维支气管镜取呼吸道细菌学标本,以防污染样本毛刷≥103 cfu/ml、支气管肺泡灌洗液≥104 cfu/ml 确定为细菌定植标准[5]。
(3)气道高反应性(airway high response,AHR) 评价标准(以下 3 条满足其中一条即诊断):① CPET 检测过程中,若肺部出现干鸣音或血氧饱和度降低大于 15%,则诊断为气道高反应性;② 若不能进行 CPET,也可在爬楼梯训练过程中(33 台阶),速度为每秒钟一个台阶,若肺部出现干鸣音或血氧饱和度降低大于 15%,也可粗略诊断为气道高反应性;③ 支气管舒张试验[4]。
(4)呼气峰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PFE) PF<250 L/min 评价标准:应用峰流速仪或哮喘检测仪发现的高危因素,PEF<250 L/min[6]。
(5)肺功能处于临界状态(marginal pulmonary function) 评价标准: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1.0 L 或一秒率(FEV1/FVC)<50%[7]。
1.2.3.2 肺康复训练方案 (1)抗感染:根据标准应用;(2)祛痰:术前 3~7 d 及术后 3~7 d; 沐舒坦 30 mg,ivgtt,Q8h 和/或吉诺通 300 mg,tid po(必需);(3)平喘或消炎:术前 3~7 d、术后 3~7 d;普米克令舒+博利康尼,4 ml+2 ml/time,2 time/d(必需);(4)激励式肺量计吸气训练:(VOLDYNE5000)患者取易于深吸气的体位,一手握住激励式肺量计,用嘴含住咬嘴并确保密闭不漏气,然后进行深慢的吸气,将黄色的浮标吸升至预设的标记点,然后屏气 2~3 s,移开咬嘴呼气。重复以上步骤,每组进行 6~10 次训练,然后休息。在非睡眠时间,每 2 h 重复一组训练,以不引起患者疲劳为宜。3~7 d(必需);(5)功率自行车运动训练:患者自行调控速度,在承受范围内逐步加快步行速度及自行车功率。运动量控制在呼吸困难指数(Borg)评分 5~7 分,若在运动过程中有明显气促、腿疲倦、血氧饱和度下降(<88%)或其它合并疾病引起身体不适则休息,待恢复原状后再继续进行训练。每次约 15~20 min,每天 2 次,疗程为 7~14 d(可选)。(6)登楼梯训练:在专业治疗师陪同下进行,在运动过程中调整呼吸节奏,采用缩唇呼吸,用力时呼气,避免闭气,稍感气促时可坚持进行,若有明显呼吸困难,则短暂休息,尽快继续运动。每次约 15~30 min,每天 2 次,疗程 3~7 d(可选)。
1.2.4 肺部并发症分类及评价标准 (1)PPC 包括肺部感染、肺栓塞、乳糜胸、皮下气肿、咯血、声音嘶哑、支气管胸膜瘘、手术后持续肺漏气、手术后胸腔积液(中到大量)和积气(肺压缩≥30%)、肺不张、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呼吸衰竭(肺部并发症分类及评价标准见表 1)。(2)肺部感染的标准:含有以下指标 3 个或以上为手术后肺炎[8-9]:① 手术后 72 h 发热,体温>38℃;或 72 h 以内体温再度升高。② 白细胞计数升高(>12~15×109/L)或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值以后的再升高,超过 10×109/L。③ 胸部影像学提示肺组织实变或不断增加的斑片状阴影。④ 咳出脓性痰液或痰培养阳性。其中如果包含 ④,仅需要其他一项即可视为手术后肺炎(postoperative pneumonia,POP)或经呼吸科会诊确定为肺部感染,并需要更换抗生素或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
1.2.5 手术方法 胸腔镜肺叶切除患者手术方法:单向式胸腔镜肺叶切除法+系统淋巴结清扫[10]。开胸患者应用常规后外侧切口,肺叶切除术+系统淋巴结清扫。系统淋巴结清扫左侧必须清扫第 5、6、7、8、9、10 组淋巴结,右侧包括第 2、3、4、7、8、9、10 组淋巴结。
1.2.6 术后处理方法 术后疼痛处理均应用镇痛泵(盐酸曲马多注射液,1~1.5 mg/h),均早期促使患者下床活动。必要时应用非甾体类止痛药(氨酚羟考酮片或布洛芬缓释胶囊)。镇痛泵于胸腔引流管拔除的同时也一起停止。两组患者均根据胸腔引流气体和液体量决定行胸部 X 线片检查时间,并根据胸部 X 线片结果决定是否拔除胸腔引流管。
1.3 血浆中 SP-D 浓度的测定
在患者入院当天、手术前 1 d、手术后第 1 d、手术后第 3 d 及出院前 1 d 5 个时间点,分别采集患者外周血 5 ml,待血液自然凝固 10~20 min,离心 20 min,2 000 转/分,收集血清,应用双抗体夹心法测定标本中SP-D水平。试验流程图见图 1。SP-D ELISA 试剂盒由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图1
试验流程图
图1
试验流程图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描述,组间比较用独立样本的t 检验或方差分析;样本在作t 检验和方差分析前均先作正态分析或方差齐性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使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生理学特征分析
患者流程见图 2,其中康复组 36 例 [男 25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63.98±8.32)岁],对照组 44 例 [男 32 例,女 12 例,平均年龄(64.58±6.71)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的病理类型、病理分期、手术方式、合并症(COPD/高血压/糖尿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康复组发生 PPC2 例(2/36,5.56%)。两组 PPC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对照组 PPC 发生率更高(10/44,22.73%);见表 2。
 图2
80 例患者随机分组流程图
图2
80 例患者随机分组流程图
2.2 两组患者高危因素及术后并发症种类分布
康复组患者 36 例,共检出高危因素 63 项,其中有 1 项高危因素患者 15 例,2 项 16 例,3 项 4 例,3 项以上 1 例;对照组患者 44 例,共检出高危因素 74 项,其中有 1 项高危因素的患者 20 例,2 项 19 例,3 项 4 例,3 项以上 1 例。两组患者术前高危因素的构成比和高危因素负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康复组发生术后并发症的患者 2 例(共 3 类并发症),对照组发生术后并发症的患者 10 例(共 15 类并发症)。并发症种类分布见表 3。
2.3 两组患者在围手术期血清 SP-D 水平变化分析
康复训练前(入院时)血清 SP-D 水平在康复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75±5.57)ng/mlvs. (31.16±7.81)ng/ml ,P=0.872],康复训练后(手术前 1 d)血清 SP-D 水平在康复组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22±3.08)ng/mlvs. (30.29±5.80)ng/ml ,P=0.000];而手术后第 1、2 天及出院时血清 SP-D 水平在康复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4,图 3a)。
 图3
患者不同指标分组围手术期血清 SP-D 水平变化的比较 a. 80 例患者按照康复/对照组分组,比较两组血清 SP-D 的变化; b. 80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c. 未行肺康复训练的 44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d. 36 例肺康复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图3
患者不同指标分组围手术期血清 SP-D 水平变化的比较 a. 80 例患者按照康复/对照组分组,比较两组血清 SP-D 的变化; b. 80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c. 未行肺康复训练的 44 例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d. 36 例肺康复患者按是否发生 PPC 分组,比较两组间血清 SP-D 的变化
2.4 80 例高危因素患者围手术期的血清 SP-D 水平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相关性
80 例肺癌合并高危因素患者按照术后是否发生 PPC,分成 PPC 组(n=12)和非 PPC 组(n=68)。PPC 组患者血清 SP-D 水平在手术前 1 d 的血清 SP-D 水平高于非 PP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1.18±5.43)ng/mlvs. (26.66±4.97)ng/ml ,P=0.005,表 5,图 3b]。
2.5 术前对照组患者血清 SP-D 水平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相关性分析
对照组患者术后发生 PPC10 例(22.73%,10/44),未发生 PPC34 例(34/44)。PPC 组患者术前(入院当天)血清 SP-D 水平高于非 PP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93±4.15)ng/mlvs. (29.81±7.47)ng/ml,P=0.045,表 6,图 3c]。
2.6 术前康复组肺癌患者血清 SP-D 水平与术后肺部并发症的相关性分析
康复组患者术后发生 PPC 2 例(5.56%,2/36),未发生 PPC 34 例(34/36)。PPC 组患者术前(入院当天和术前 1 d)血清 SP-D 水平变化幅度[(29.78±2.52)ng/mlvs. (27.84±3.05)ng/ml]低于非 PPC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80±5.48)ng/mlvs. (24.18±3.12)ng/ml,表 7,图 3d]。
3 讨论
已有研究证实[7,11],围手术期肺康复训练可以改善患者心肺状态,减低 PPC 发生率。如何解释肺康复训练降低 PPC 发生率的机制,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12-14]。目前相对一致的结果是肺康复训练可以改善患者运动耐力(6 分钟步行距离、疲劳指数)和呼吸困难指数[15-16],而呼吸功能各项指标在肺康复前后的变化则有较大争议[7,17-18]。
不同于常规临床病史和生理学参数,生物标志物在不同的层面揭示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可以连同临床观察指标一起更好地解释临床现象的原因。Paone 等[19]报道了使用无创通气治疗 COPD 的长期效果,发现干预手段可以导致血清炎症因子的变化。Morano 等[20]首次采用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比较了肺康复对血清纤维蛋白原水平的影响,结果提示对于等待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前肺康复可以降低血清纤维蛋白原的水平,提高运动耐力指标,改善生活质量。纤维蛋白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炎症因子,与 COPD 和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相关,但其是下游反应产物,由多部位分泌,特异性较差[21-22]。由靶器官分泌的特异性蛋白特异性更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Jehn 等[23]应用血清前心房利钠肽和肾上腺髓质激素水平预测稳定期 COPD 患者发生心脏事件的风险,开创了原因靶器官蛋白作为生物标志物预测疾病发生的先河。SP-D 也被用于预测 COPD 恶化的风险[24]。SP-D 是由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分泌的一类糖蛋白,与肺内的天然免疫有关,在肺泡通透性增加的情况下会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从而得以在外周血液中检测到[25]。我们的研究首次引入血清 SP-D 研究肺康复训练对其血清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康复组患者手术前 1 d(康复后)的血清 SP-D 水平下降幅度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提示术前肺康复训练可以降低肺癌手术患者血清 SP-D 水平,SP-D 在康复前后的变化与手术后 PPC 的发生相关联。
SP-D 是水溶性蛋白,除参与肺泡张力的维持外,还与机体和肺的免疫功能和炎症调节相关,参与了肺的免疫调节及病原体的吞噬及凋亡机制[26],外源性因素可以影响肺组织 SP-D 的表达水平[27],在肺康复前后血清 SP-D 水平的变化可以间接反映肺康复训练对肺功能各项指标的变化。结合目前对于肺康复是否改善肺呼吸功能指标的争论,我们认为肺康复训练不仅改善了肺的呼吸功能,同时伴随变化的还可能有肺组织局部通透性和免疫状态。在这一点上,部分关于肺康复对其他炎症因子水平变化的研究佐证了我们的观点[28-29]。
我们的试验首次研究了血清 SP-D 水平在肺癌患者康复及手术前后的变化,结果显示:不管康复与否,肺叶切除以后血清 SP-D 水平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手术后切除肺叶,减少了 SP-D 的直接分泌有关。但其下降的比例与手术后肺组织损失比例不成正比,这可能与手术后应激、局部炎症反应、手术后药物的使用等多种因素有关。
将患者按照有无 PPC 分组,研究 PPC 与围手术期血清 SP-D 的变化关系,结果发现,全组 80 例患者(无论是否肺康复训练)按有无 PPC 分组后,并发症组患者血清 SP-D 水平在手术前 1 d 的血清 SP-D 水平显著高于无并发症组(P=0.005),提示手术前即时的血清 SP-D 水平对手术后并发症预测有一定的作用。
研究进一步将 80 例患者分层研究的结果发现:(1)未接受肺康复训练的患者 44 例按有无 PPC 分组,两组患者仅在入院当天血清 SP-D 浓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他节点之间血清 SP-D 浓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术前血清 SP-D 水平较高是 PPC 的危险因素。(2)接受肺康复训练的患者 36 例中并发症发生组患者术前(入院当天和术前 1 d)血清 SP-D 水平变化幅度显著低于非 PPC 组,提示血清 SP-D 水平可以反映肺康复的效果,并与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相关。
综上所述,术前肺康复训练可以降低肺癌合并高危因素患者术后并发症,血清 SP-D 水平变化程度可作为肺康复训练的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