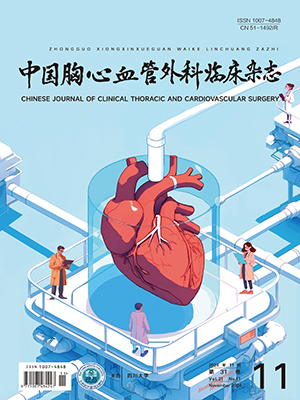引用本文: 石娟, 马名嘉, 魏翔. 马方综合征合并胸腹主动脉疾病的治疗策略选择.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0, 27(7): 742-748. doi: 10.7507/1007-4848.201910036 复制
马方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结缔组织疾病,发病率为 1/5 000~1/10 000,25%~30% 的患者为散发病例,可累及多个系统,主要表现在心血管系统、骨骼系统、眼和神经系统等多个方面[1]。动脉瘤或夹层形成及破裂是马方综合征患者最为致命的并发症。自 1968 年 Bentall 等[2]最先提出带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治疗马方综合征患者以来,使该类患者的预期寿命得以延长,Bentall 术迅速成为治疗马方综合征患者主动脉窦部病变的标准术式。但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鲜有报道。目前各国学者仍主张采用开放的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TAAAR)来治疗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3],但随着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发展,TEVAR 应用于马方综合征患者也有了一小系列研究和病例报道,但长期随访数据有限。本研究通过回顾性研究评价 TEVAR 与 TAAAR 的远期疗效,分析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治疗策略,给临床治疗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于我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接受治疗的马方综合征合并胸腹主动脉疾病 2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3 例、女 14 例,年龄(32.2±8.6)岁。所有患者主动脉夹层及分型通过胸腹主动脉 CT 血管造影(CTA)检查确诊。诊断标准:主动脉夹层破口位于左锁骨下动脉以远,夹层未累及升主动脉及主动脉弓部。马方综合征的诊断主要依靠 Ghent 标准,以临床体检、辅助影像学检查以及家族病史和 FBN1 基因突变的检查来明确。
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包括身高、体重、年龄、性别、手术方式、脊髓缺血时间、腹腔脏器缺血时间、术后早期死亡、术后早期并发症及晚期死亡和晚期并发症,以及患者再入院及再手术等指标。术后呼吸功能不全定义为机械辅助通气时间>48 h,术后肾功能不全定义为肌酐值>221 μmol/L,术后肝功能不全定义为谷丙转氨酶高于正常值上限 4 倍。术后早期死亡定义为术后 30 d 内死亡。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定义为术后出现肢体运动或感觉障碍,症状在出院前恢复。心血管不良事件定义为患者因为主动脉或者心脏病变再次接受手术治疗。
该研究纳入符合马方综合征的 Ghent 诊断标准的 Stanford B 型夹层患者,排除(1)因 Stanford B 型夹层在外院已接受治疗的;(2)弓部或升主动脉巨大动脉瘤;(3)Stanford B 型夹层逆行剥离并累及到 2 支以上头臂血管的患者。
1.2 手术方法
手术方式由主刀医生根据病情及病变情况选择。主要包括单泵辅助输血胸腹主动脉联合置换和血管腔内治疗两种治疗手段。
单泵辅助输血 TAAAR:患者取右侧卧位,取左后外侧胸腹联合切口,经左侧第 4~7 肋间进胸,游离胸降主动脉至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切断肋弓,弧形切开膈肌,远端在腹膜后游离腹主动脉至双侧髂总动脉。全身肝素化后,取四分支人工血管(Maquet,美国)进行血管置换。首先将人工血管两分支(10 mm)分别与左、右髂总动脉端侧吻合,将另一分支(8 mm)连接体外循环机单泵,阻断另一分支及主干两端,建立输血通道。体外循环贮血罐内预充血浆及红细胞,心内吸引回收术中失血。充分游离主动脉弓降部,在靠近左锁骨下动脉起始处以两把阻断钳直接阻断胸降主动脉,利用单泵输血通道维持下半身血压至 40~50 mm Hg,将四分支人工血管主干与胸降主动脉起始部行端端吻合,移除近端阻断钳。经人工血管恢复全身血液供应。在腹腔干上方阻断腹主动脉,纵行剖开胸主动脉瘤体,修剪保留 T6~L1 肋间动脉床,本中心早期将自身血管缝合成管状重建肋间动脉,亦可应用相应大小的人工血管片缝合在血管床上,重建肋间动脉。利用四分支血管的一支 8 mm 分支重建肋间动脉,恢复脊髓供血。将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左、右肾动脉开口修剪为岛状血管片,与四分支血管主干远端吻合,恢复腹腔脏器供血,结扎灌注用分支。腰动脉、肠系膜下动脉等血管在腹主动脉开口予以缝扎止血。血管重建完成后鱼精蛋白中和,胸腹腔仔细检查止血。置入腹膜后引流管及左侧胸腔引流管各 1 根。
TEVAR:患者取仰卧位,常规选股动脉入路,分离股动脉,经股动脉置入导管行主动脉造影,确定破口位置及测量主动脉直径以及支架覆盖范围、长度,根据测量结果选择直径和长度适当的覆膜支架,控制性降压,通过超硬导丝将支架(上海微创公司,中国)送至预定位置,防止支架移位,逐渐准确释放支架到目标位置,退出释放系统,再次行主动脉造影后退出导丝,缝合股动脉,仔细止血后缝合皮肤。手术成功的标准:支架释放后立即造影,显示夹层破口完全封闭,真腔较术前明显扩大,血流加速,无内漏,或者虽有内漏,但造影剂进入假腔减少 70% 以上,各主要分支动脉无缺血。
1.3 随访
术后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及以后每年进行门诊复查及电话随访。门诊检查包括心脏彩超、胸腹主动脉 CTA 等辅助检查。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术后生存时间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术后生存时间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编号:TJ-C20190601。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相较于普通主动脉夹层患者人群,马方综合征患者男女比例相当,发病更加年轻,8 例患者行 TEVAR,TEVAR 治疗指征为:妊娠 3 例,急性下肢缺血 2 例,急性胃肠道缺血伴消化道出血 2 例,急性肝功能损伤 1 例。19 例患者行 TAAAR,其中 7 例既往因升主动脉病变已行一期手术治疗,5 例行 Bentall 术(1 例行 Bentall+右中叶肺大疱切除术),2 例行孙氏手术。2 例患者高血压病史,3 例妊娠患者,均为晚期妊娠,1 例夹层源性右肾萎缩,但未达透析标准。其余患者术前均无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等慢性病史。急性期(发病 2 周内)手术 8 例,均为 TEVAR,慢性期手术 19 例,均为 TAAAR;见表 1。
 /例)
/例)
2.2 围手术期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19 例行 TAAAR 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524.74±106.46)min,体外循环时间(110.95±29.93)min,脊髓缺血时间(19.33±3.44)min,腹腔脏器缺血时间(19.83±1.94)min;见表 2。8 例患者行 TEVAR,3 例为局部麻醉,5 例全身麻醉下手术,手术成功率为 100.0%。其中 3 例妊娠患者 1 例同期行剖宫产术,2 例继续妊娠(1 例 TEVAR 术后 16 d 复查 CTA 发现逆撕为 A 型主动脉夹层,家属放弃治疗,行剖宫产术后夹层破裂死亡)。早期死亡 2 例,均发生在行 TEVAR 患者,早期死亡率 7.4%。分析死亡原因,1 例死于夹层破裂,1 例死于产褥期感染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突发心跳骤停。全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37.0%,再次气管插管 4 例(14.8%),TAAAR 与 TEVAR 中各 2 例;呼吸功能不全 5 例(18.5%),主要发生在 TAAAR 组中(1 例 vs. 4 例);肾功能不全及肝功能不全也主要发生在 TAAAR 组中(0 例 vs. 2 例,1 例 vs. 3 例)。全组无截瘫患者,TAAAR 组中 2 例出现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其中 1 例表现为双下肢轻瘫,另 1 例患者表现为下肢麻木,二者均在出院前好转。
 /例)
/例)
2.3 随访结果
全组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率 100.0%,随访时间(47.6±36.7)个月。随访期间,TEVAR 中 3 例在 3 个月内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分别于术后 24 d、26 d、79 d 行孙氏手术,其中 2 例为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1 例 1 年后发现主动脉根部增宽行 Bentall 术。TAAAR 中 1 例术后 1 年死于脑卒中,2 例分别于 1 年和 4 年后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术,1 例 7 年后行 Bentall 术,1 例 3 期行二尖瓣置换术,1 例因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行腹壁切口疝修补术。术后 3 年免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 TEVAR 为 18.8%±15.8%,TAAAR 为 86.1%±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图 1。术后 3 年生存率 TEVAR 为 75.0%±15.3%,TAAAR 为 94.7%±5.1%;见图 2。
 图1
免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曲线
图1
免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曲线
 图2
术后患者生存曲线
图2
术后患者生存曲线
3 讨论
马方综合征患者有心血管系统异常者占 40%~60%[4],其中 31% 的马方综合征患者需要对胸降主动脉及远端主动脉进行干预,有 18% 的患者初次干预是在胸降主动脉及远端主动脉[5]。随着血管内修复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接受 TEVAR,同时也增加了 TEVAR 术中马方综合征患者。虽然有大量的病例报告报道了很高的手术成功率,但很少有关于马方综合征患者血管内手术中长期结果的数据。
Ince 等[6]报道了 6 例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其中 5 例已行主动脉根部置换,随访 12~74 个月,其中 3 例后期行开放手术,1 例死亡。Nordon 等[7]报道了 7 例接受 TEVAR 的马方综合征患者,所有患者均已接受主动脉根部的干预,早期死亡率 14.0%(1/7)。中位随访时间 16 个月,6 例中有 2 例(33.3%)需要再次干预,随访期间所有患者的胸主动脉均持续扩张,主动脉中位生长速度为 7.2 mm/年。Dong 等[8]报道了 432 例行 TEVAR 后 11 例出现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其中 3 例(27.3%)为马方综合征患者,2 例死亡,认为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是马方综合征 TEVAR 术后最常见并发症。Waterman 等[9]报道了 16 例行 TEVAR 马方综合征患者,4 例(25.0%)死亡,5 例转为开放手术。与本中心研究结果类似,8 例患者行 TEVAR,3 例患者 3 个月内再发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手术,其中 1 例因夹层破裂死亡。马方综合征患者由于其特殊的病因,动脉壁薄弱,而覆膜支架系统在释放后需要靠自身张力锚定在血管内壁上,使马方综合征患者在 TEVAR 后易逆撕为 A 型夹层、破裂或出现内漏,由于远端管腔仍在继续扩大仍需要再次手术干预远端主动脉。因此,TEVAR 不是马方综合征患者初次出现 Stanford B 型夹层的首选治疗。
有部分研究者将 TEVAR 用于特殊患者并进行了病例报道,Eid-Lidt 等[10]报道了 10 例有开放手术高风险的马方综合征合并慢性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平均随访(59.6±38.9)个月,累计死亡率为 20%,晚期死亡率为 11.1%,继发性内漏发生率为 44.4%,晚期再介入率为 33.3%。8 年免于心血管死亡的存活率为 80.0%,与目前开放手术治疗相当,认为 TEVAR 适用于存在开放手术高风险的患者。Cooper 等[11]报道了 3 例行 TEVAR 的马方综合征患者,第 1 例为已行 TAAAR,术后 3 个月肋间动脉补片出现假性动脉瘤患者;第 2、3 例为慢性 Stanford B 型夹层,但 1 例腹主动脉最大直径只有 4.5 cm,1 例膈肌水平处主动脉 4 cm,3 例 3 个月内随访结果满意,第 2 例 24 个月后仅接受腹部段的开放性手术。赵纪春等[12]报道了 1 例脊柱和胸廓极度变形扭曲和既往胸腔手术病史的马方综合征患者,采用全内脏动脉重建联合腔内覆膜支架修复的杂交手术方式进行治疗,术后随访,支架未见内漏且重建内脏动脉血流通畅,主动脉未见新发动脉瘤,患者无任何不良症状及体征,效果良好。唐骁等[13]报道先行 TEVAR,随访后二期行 TAAAR,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认为先行 TEVAR 后二期行 TAAAR 时无需阻断降主动脉,缩短了脊髓的缺血时间,而且夹层进入慢性期,脊髓血供已有充足的时间建立侧枝循环,同时降低了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程度。根据目前的建议,我们认为 TEVAR 可以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应用,虽不推荐为首选治疗方案,但可以为开放手术高风险患者,如有复杂或反复胸腔手术史、慢性夹层假腔血栓形成并钙化严重、行开放手术截瘫风险高、脊柱及胸廓畸形严重等复杂患者提供治疗方案,并从中获益。急性脏器灌注不良患者,如本研究 2 例下肢缺血、2 例急性肠道缺血及 1 例急性肝脏灌注不足患者,此时急需开通脏器循环,TEVAR 可在较短时间内封堵破口,增加真腔血流,恢复脏器血供,作为患者向后期行开放手术的过渡阶段,但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症状及影像学变化,必要时及时行开放手术干预。而杂交手术中支架两端已行人工血管置换,为支架两端可置于人工血管内的患者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手术方式。
马方综合征患者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起病凶险,进展迅速,及早根据主动脉夹层类型、母儿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是挽救患者及胎儿生命的关键。Lipscomb 等[14]认为若主动脉直径≥4 cm 或主动脉直径在稳定增长,妊娠期间发生主动脉夹层的风险较高。相较于妊娠合并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来说,妊娠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较为少见。对于这类患者目前多主张早期行保守治疗,包括积极控制血压、止痛等,待胎儿发育成熟后,择期行剖宫产术及手术治疗主动脉夹层。若合并有主动脉夹层破裂或脏器缺血(包括子宫缺血或胎盘功能不全)等并发症,以及保守治疗下血压控制不佳或夹层持续发展等,则有急诊手术的指征[15]。腔内的 TEVAR 为微创修复 B 型主动脉夹层破口提供了可能,避免了开放手术的创伤,同时也为妊娠患者创造了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环境[16]。但 TEVAR 治疗妊娠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仍存在风险,本中心 3 例妊娠患者,1 例 TEVAR 术后 28 d 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入院,同期行孙氏术加剖宫产术;1 例同期行 TEVAR 加剖宫产术,术后出现产褥期感染,多器官功能障碍最后心跳骤停死亡;1 例住院期间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行剖宫产术后家属放弃治疗,夹层破裂死亡。孕期进行心血管手术对母体和胎儿都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但随着近年来心血管手术及与之相关的体外循环技术的发展,使这类手术的安全性大大提高。由产科、心脏外科、心脏内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制定个体化方案,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合并主动脉夹层的马方综合征孕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17]。
TAAAR 被认为是治疗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的金标准[18]。Preventza 等[19]报道应用 TAAAR 治疗 Ⅲ 型主动脉夹层 239 例,30 d 死亡率是 5.9%(14 例)。而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TAAAR 的成功率也很高,Kalkat 等[20]报道 22 例马方综合征合并远端主动脉夹层,19 例接受开放手术治疗,没有早期死亡、截瘫及肾功能衰竭病例。LeMaire 等[21]报道了 81 例经证实的马方综合征患者的 30 d 死亡率为 2%,卒中发生率为 1%,截瘫发生率为 5%。张良等[22]报道采用髂动脉插管和四分支血管插管,单泵双管灌注,在常温非体外循环下进行 TAAAR 的方法。相较于深低温停循环组,常温下手术缩短了整体手术时间,降低了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本中心经过实践,进一步简化操作,将四分支血管两支首先与髂动脉吻合,用于渗血回收以及术中输血。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同样较低。孙立忠等[23]报道了常温非体外循环下的 TAAAR 早期死亡率为 3.7%,采用各种脊髓保护措施后脊髓缺血的发生率为 4.76%,肺部并发症发生率为 11.54%,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为 3.85%。本研究 TAAAR 组所有患者全部顺利出院,无术后 30 d 死亡病例,无截瘫患者,呼吸功能不全 4 例(21.1%),肾功能不全 2 例(10.5%),均未达到透析指标,肝功能不全 3 例(15.8%)。此外,由于马方综合征患者血管先天缺陷,肋间动脉重建后有扩张成瘤的可能[24]。我们主张应尽量减少自身动脉壁的残留,避免游离血管周围组织,将修剪后的血管片与人工血管原位吻合,重建肋间动脉血供。在随访过程中,采用补片法原位重建的肋间动脉均未出现瘤样扩张。
现有文献表明,TEVAR 可以安全地进行,短期内并发症少,死亡率低。然而,在这方面,与现有的开放技术相比,微创方法所带来的好处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并不那么明显,可能与马方综合征患者通常较年轻,生理储备大且很少合并慢性病有关。因此开放的非体外循环下 TAAAR 为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可靠治疗手段,而且开放手术适合于大部分胸腹主动脉瘤或 Stanford B 型夹层的患者,尤其是对于马方综合征这类年轻又不合并其它慢性疾病患者。开放手术并未引起这类患者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增高。TEVAR 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应仅限于支架可置于已置换主动脉段两个着陆区、开放手术高风险或作为向开放手术过渡的患者。对于妊娠患者,需由产科、心脏外科、心脏内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根据孕周及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方案,降低孕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石娟参与研究与文章撰写;马名嘉参与数据分析;魏翔参与文章修改。
马方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结缔组织疾病,发病率为 1/5 000~1/10 000,25%~30% 的患者为散发病例,可累及多个系统,主要表现在心血管系统、骨骼系统、眼和神经系统等多个方面[1]。动脉瘤或夹层形成及破裂是马方综合征患者最为致命的并发症。自 1968 年 Bentall 等[2]最先提出带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治疗马方综合征患者以来,使该类患者的预期寿命得以延长,Bentall 术迅速成为治疗马方综合征患者主动脉窦部病变的标准术式。但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鲜有报道。目前各国学者仍主张采用开放的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TAAAR)来治疗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3],但随着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发展,TEVAR 应用于马方综合征患者也有了一小系列研究和病例报道,但长期随访数据有限。本研究通过回顾性研究评价 TEVAR 与 TAAAR 的远期疗效,分析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治疗策略,给临床治疗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于我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接受治疗的马方综合征合并胸腹主动脉疾病 2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3 例、女 14 例,年龄(32.2±8.6)岁。所有患者主动脉夹层及分型通过胸腹主动脉 CT 血管造影(CTA)检查确诊。诊断标准:主动脉夹层破口位于左锁骨下动脉以远,夹层未累及升主动脉及主动脉弓部。马方综合征的诊断主要依靠 Ghent 标准,以临床体检、辅助影像学检查以及家族病史和 FBN1 基因突变的检查来明确。
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包括身高、体重、年龄、性别、手术方式、脊髓缺血时间、腹腔脏器缺血时间、术后早期死亡、术后早期并发症及晚期死亡和晚期并发症,以及患者再入院及再手术等指标。术后呼吸功能不全定义为机械辅助通气时间>48 h,术后肾功能不全定义为肌酐值>221 μmol/L,术后肝功能不全定义为谷丙转氨酶高于正常值上限 4 倍。术后早期死亡定义为术后 30 d 内死亡。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定义为术后出现肢体运动或感觉障碍,症状在出院前恢复。心血管不良事件定义为患者因为主动脉或者心脏病变再次接受手术治疗。
该研究纳入符合马方综合征的 Ghent 诊断标准的 Stanford B 型夹层患者,排除(1)因 Stanford B 型夹层在外院已接受治疗的;(2)弓部或升主动脉巨大动脉瘤;(3)Stanford B 型夹层逆行剥离并累及到 2 支以上头臂血管的患者。
1.2 手术方法
手术方式由主刀医生根据病情及病变情况选择。主要包括单泵辅助输血胸腹主动脉联合置换和血管腔内治疗两种治疗手段。
单泵辅助输血 TAAAR:患者取右侧卧位,取左后外侧胸腹联合切口,经左侧第 4~7 肋间进胸,游离胸降主动脉至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切断肋弓,弧形切开膈肌,远端在腹膜后游离腹主动脉至双侧髂总动脉。全身肝素化后,取四分支人工血管(Maquet,美国)进行血管置换。首先将人工血管两分支(10 mm)分别与左、右髂总动脉端侧吻合,将另一分支(8 mm)连接体外循环机单泵,阻断另一分支及主干两端,建立输血通道。体外循环贮血罐内预充血浆及红细胞,心内吸引回收术中失血。充分游离主动脉弓降部,在靠近左锁骨下动脉起始处以两把阻断钳直接阻断胸降主动脉,利用单泵输血通道维持下半身血压至 40~50 mm Hg,将四分支人工血管主干与胸降主动脉起始部行端端吻合,移除近端阻断钳。经人工血管恢复全身血液供应。在腹腔干上方阻断腹主动脉,纵行剖开胸主动脉瘤体,修剪保留 T6~L1 肋间动脉床,本中心早期将自身血管缝合成管状重建肋间动脉,亦可应用相应大小的人工血管片缝合在血管床上,重建肋间动脉。利用四分支血管的一支 8 mm 分支重建肋间动脉,恢复脊髓供血。将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左、右肾动脉开口修剪为岛状血管片,与四分支血管主干远端吻合,恢复腹腔脏器供血,结扎灌注用分支。腰动脉、肠系膜下动脉等血管在腹主动脉开口予以缝扎止血。血管重建完成后鱼精蛋白中和,胸腹腔仔细检查止血。置入腹膜后引流管及左侧胸腔引流管各 1 根。
TEVAR:患者取仰卧位,常规选股动脉入路,分离股动脉,经股动脉置入导管行主动脉造影,确定破口位置及测量主动脉直径以及支架覆盖范围、长度,根据测量结果选择直径和长度适当的覆膜支架,控制性降压,通过超硬导丝将支架(上海微创公司,中国)送至预定位置,防止支架移位,逐渐准确释放支架到目标位置,退出释放系统,再次行主动脉造影后退出导丝,缝合股动脉,仔细止血后缝合皮肤。手术成功的标准:支架释放后立即造影,显示夹层破口完全封闭,真腔较术前明显扩大,血流加速,无内漏,或者虽有内漏,但造影剂进入假腔减少 70% 以上,各主要分支动脉无缺血。
1.3 随访
术后 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及以后每年进行门诊复查及电话随访。门诊检查包括心脏彩超、胸腹主动脉 CTA 等辅助检查。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术后生存时间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术后生存时间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编号:TJ-C20190601。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相较于普通主动脉夹层患者人群,马方综合征患者男女比例相当,发病更加年轻,8 例患者行 TEVAR,TEVAR 治疗指征为:妊娠 3 例,急性下肢缺血 2 例,急性胃肠道缺血伴消化道出血 2 例,急性肝功能损伤 1 例。19 例患者行 TAAAR,其中 7 例既往因升主动脉病变已行一期手术治疗,5 例行 Bentall 术(1 例行 Bentall+右中叶肺大疱切除术),2 例行孙氏手术。2 例患者高血压病史,3 例妊娠患者,均为晚期妊娠,1 例夹层源性右肾萎缩,但未达透析标准。其余患者术前均无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等慢性病史。急性期(发病 2 周内)手术 8 例,均为 TEVAR,慢性期手术 19 例,均为 TAAAR;见表 1。
 /例)
/例)
2.2 围手术期结果
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19 例行 TAAAR 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524.74±106.46)min,体外循环时间(110.95±29.93)min,脊髓缺血时间(19.33±3.44)min,腹腔脏器缺血时间(19.83±1.94)min;见表 2。8 例患者行 TEVAR,3 例为局部麻醉,5 例全身麻醉下手术,手术成功率为 100.0%。其中 3 例妊娠患者 1 例同期行剖宫产术,2 例继续妊娠(1 例 TEVAR 术后 16 d 复查 CTA 发现逆撕为 A 型主动脉夹层,家属放弃治疗,行剖宫产术后夹层破裂死亡)。早期死亡 2 例,均发生在行 TEVAR 患者,早期死亡率 7.4%。分析死亡原因,1 例死于夹层破裂,1 例死于产褥期感染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突发心跳骤停。全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37.0%,再次气管插管 4 例(14.8%),TAAAR 与 TEVAR 中各 2 例;呼吸功能不全 5 例(18.5%),主要发生在 TAAAR 组中(1 例 vs. 4 例);肾功能不全及肝功能不全也主要发生在 TAAAR 组中(0 例 vs. 2 例,1 例 vs. 3 例)。全组无截瘫患者,TAAAR 组中 2 例出现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其中 1 例表现为双下肢轻瘫,另 1 例患者表现为下肢麻木,二者均在出院前好转。
 /例)
/例)
2.3 随访结果
全组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率 100.0%,随访时间(47.6±36.7)个月。随访期间,TEVAR 中 3 例在 3 个月内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分别于术后 24 d、26 d、79 d 行孙氏手术,其中 2 例为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1 例 1 年后发现主动脉根部增宽行 Bentall 术。TAAAR 中 1 例术后 1 年死于脑卒中,2 例分别于 1 年和 4 年后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术,1 例 7 年后行 Bentall 术,1 例 3 期行二尖瓣置换术,1 例因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行腹壁切口疝修补术。术后 3 年免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 TEVAR 为 18.8%±15.8%,TAAAR 为 86.1%±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图 1。术后 3 年生存率 TEVAR 为 75.0%±15.3%,TAAAR 为 94.7%±5.1%;见图 2。
 图1
免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曲线
图1
免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曲线
 图2
术后患者生存曲线
图2
术后患者生存曲线
3 讨论
马方综合征患者有心血管系统异常者占 40%~60%[4],其中 31% 的马方综合征患者需要对胸降主动脉及远端主动脉进行干预,有 18% 的患者初次干预是在胸降主动脉及远端主动脉[5]。随着血管内修复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接受 TEVAR,同时也增加了 TEVAR 术中马方综合征患者。虽然有大量的病例报告报道了很高的手术成功率,但很少有关于马方综合征患者血管内手术中长期结果的数据。
Ince 等[6]报道了 6 例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其中 5 例已行主动脉根部置换,随访 12~74 个月,其中 3 例后期行开放手术,1 例死亡。Nordon 等[7]报道了 7 例接受 TEVAR 的马方综合征患者,所有患者均已接受主动脉根部的干预,早期死亡率 14.0%(1/7)。中位随访时间 16 个月,6 例中有 2 例(33.3%)需要再次干预,随访期间所有患者的胸主动脉均持续扩张,主动脉中位生长速度为 7.2 mm/年。Dong 等[8]报道了 432 例行 TEVAR 后 11 例出现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其中 3 例(27.3%)为马方综合征患者,2 例死亡,认为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是马方综合征 TEVAR 术后最常见并发症。Waterman 等[9]报道了 16 例行 TEVAR 马方综合征患者,4 例(25.0%)死亡,5 例转为开放手术。与本中心研究结果类似,8 例患者行 TEVAR,3 例患者 3 个月内再发逆撕型 A 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手术,其中 1 例因夹层破裂死亡。马方综合征患者由于其特殊的病因,动脉壁薄弱,而覆膜支架系统在释放后需要靠自身张力锚定在血管内壁上,使马方综合征患者在 TEVAR 后易逆撕为 A 型夹层、破裂或出现内漏,由于远端管腔仍在继续扩大仍需要再次手术干预远端主动脉。因此,TEVAR 不是马方综合征患者初次出现 Stanford B 型夹层的首选治疗。
有部分研究者将 TEVAR 用于特殊患者并进行了病例报道,Eid-Lidt 等[10]报道了 10 例有开放手术高风险的马方综合征合并慢性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平均随访(59.6±38.9)个月,累计死亡率为 20%,晚期死亡率为 11.1%,继发性内漏发生率为 44.4%,晚期再介入率为 33.3%。8 年免于心血管死亡的存活率为 80.0%,与目前开放手术治疗相当,认为 TEVAR 适用于存在开放手术高风险的患者。Cooper 等[11]报道了 3 例行 TEVAR 的马方综合征患者,第 1 例为已行 TAAAR,术后 3 个月肋间动脉补片出现假性动脉瘤患者;第 2、3 例为慢性 Stanford B 型夹层,但 1 例腹主动脉最大直径只有 4.5 cm,1 例膈肌水平处主动脉 4 cm,3 例 3 个月内随访结果满意,第 2 例 24 个月后仅接受腹部段的开放性手术。赵纪春等[12]报道了 1 例脊柱和胸廓极度变形扭曲和既往胸腔手术病史的马方综合征患者,采用全内脏动脉重建联合腔内覆膜支架修复的杂交手术方式进行治疗,术后随访,支架未见内漏且重建内脏动脉血流通畅,主动脉未见新发动脉瘤,患者无任何不良症状及体征,效果良好。唐骁等[13]报道先行 TEVAR,随访后二期行 TAAAR,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认为先行 TEVAR 后二期行 TAAAR 时无需阻断降主动脉,缩短了脊髓的缺血时间,而且夹层进入慢性期,脊髓血供已有充足的时间建立侧枝循环,同时降低了患者全身炎症反应程度。根据目前的建议,我们认为 TEVAR 可以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应用,虽不推荐为首选治疗方案,但可以为开放手术高风险患者,如有复杂或反复胸腔手术史、慢性夹层假腔血栓形成并钙化严重、行开放手术截瘫风险高、脊柱及胸廓畸形严重等复杂患者提供治疗方案,并从中获益。急性脏器灌注不良患者,如本研究 2 例下肢缺血、2 例急性肠道缺血及 1 例急性肝脏灌注不足患者,此时急需开通脏器循环,TEVAR 可在较短时间内封堵破口,增加真腔血流,恢复脏器血供,作为患者向后期行开放手术的过渡阶段,但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症状及影像学变化,必要时及时行开放手术干预。而杂交手术中支架两端已行人工血管置换,为支架两端可置于人工血管内的患者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手术方式。
马方综合征患者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起病凶险,进展迅速,及早根据主动脉夹层类型、母儿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是挽救患者及胎儿生命的关键。Lipscomb 等[14]认为若主动脉直径≥4 cm 或主动脉直径在稳定增长,妊娠期间发生主动脉夹层的风险较高。相较于妊娠合并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来说,妊娠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较为少见。对于这类患者目前多主张早期行保守治疗,包括积极控制血压、止痛等,待胎儿发育成熟后,择期行剖宫产术及手术治疗主动脉夹层。若合并有主动脉夹层破裂或脏器缺血(包括子宫缺血或胎盘功能不全)等并发症,以及保守治疗下血压控制不佳或夹层持续发展等,则有急诊手术的指征[15]。腔内的 TEVAR 为微创修复 B 型主动脉夹层破口提供了可能,避免了开放手术的创伤,同时也为妊娠患者创造了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环境[16]。但 TEVAR 治疗妊娠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仍存在风险,本中心 3 例妊娠患者,1 例 TEVAR 术后 28 d 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入院,同期行孙氏术加剖宫产术;1 例同期行 TEVAR 加剖宫产术,术后出现产褥期感染,多器官功能障碍最后心跳骤停死亡;1 例住院期间再发 A 型主动脉夹层,行剖宫产术后家属放弃治疗,夹层破裂死亡。孕期进行心血管手术对母体和胎儿都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但随着近年来心血管手术及与之相关的体外循环技术的发展,使这类手术的安全性大大提高。由产科、心脏外科、心脏内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制定个体化方案,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合并主动脉夹层的马方综合征孕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17]。
TAAAR 被认为是治疗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的金标准[18]。Preventza 等[19]报道应用 TAAAR 治疗 Ⅲ 型主动脉夹层 239 例,30 d 死亡率是 5.9%(14 例)。而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TAAAR 的成功率也很高,Kalkat 等[20]报道 22 例马方综合征合并远端主动脉夹层,19 例接受开放手术治疗,没有早期死亡、截瘫及肾功能衰竭病例。LeMaire 等[21]报道了 81 例经证实的马方综合征患者的 30 d 死亡率为 2%,卒中发生率为 1%,截瘫发生率为 5%。张良等[22]报道采用髂动脉插管和四分支血管插管,单泵双管灌注,在常温非体外循环下进行 TAAAR 的方法。相较于深低温停循环组,常温下手术缩短了整体手术时间,降低了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本中心经过实践,进一步简化操作,将四分支血管两支首先与髂动脉吻合,用于渗血回收以及术中输血。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同样较低。孙立忠等[23]报道了常温非体外循环下的 TAAAR 早期死亡率为 3.7%,采用各种脊髓保护措施后脊髓缺血的发生率为 4.76%,肺部并发症发生率为 11.54%,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为 3.85%。本研究 TAAAR 组所有患者全部顺利出院,无术后 30 d 死亡病例,无截瘫患者,呼吸功能不全 4 例(21.1%),肾功能不全 2 例(10.5%),均未达到透析指标,肝功能不全 3 例(15.8%)。此外,由于马方综合征患者血管先天缺陷,肋间动脉重建后有扩张成瘤的可能[24]。我们主张应尽量减少自身动脉壁的残留,避免游离血管周围组织,将修剪后的血管片与人工血管原位吻合,重建肋间动脉血供。在随访过程中,采用补片法原位重建的肋间动脉均未出现瘤样扩张。
现有文献表明,TEVAR 可以安全地进行,短期内并发症少,死亡率低。然而,在这方面,与现有的开放技术相比,微创方法所带来的好处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并不那么明显,可能与马方综合征患者通常较年轻,生理储备大且很少合并慢性病有关。因此开放的非体外循环下 TAAAR 为马方综合征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可靠治疗手段,而且开放手术适合于大部分胸腹主动脉瘤或 Stanford B 型夹层的患者,尤其是对于马方综合征这类年轻又不合并其它慢性疾病患者。开放手术并未引起这类患者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的增高。TEVAR 在马方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应仅限于支架可置于已置换主动脉段两个着陆区、开放手术高风险或作为向开放手术过渡的患者。对于妊娠患者,需由产科、心脏外科、心脏内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根据孕周及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方案,降低孕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石娟参与研究与文章撰写;马名嘉参与数据分析;魏翔参与文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