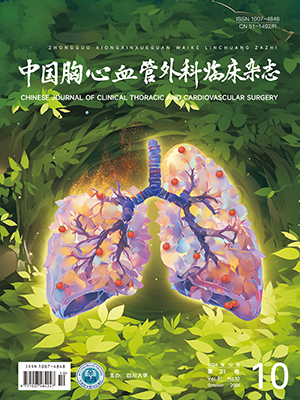引用本文: 温臣, 朱放, 张茜, 胡辰, 陈浩, 仇黎生, 施国丞, 张浩, 祝忠群, 陈会文. 混合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外科治疗.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0, 27(4): 415-420. doi: 10.7507/1007-4848.201911042 复制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指全部肺静脉未能与左心房连接,其中混合型十分罕见,约占 10%[1]。手术修复 TAPVC 已取得良好效果,但是混合型手术后死亡和肺静脉梗阻的发生率仍然很高[2]。本文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06~2018 年手术矫正混合型 TAPVC 患者的效果,为该种罕见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手术治疗提供经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6~2018 年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行外科手术治疗混合型 TAPVC 患者(排除合并单心室、右心室双出口等患者)共 51 例,其中男 35 例、女 16 例,中位年龄 102.0(59.0,181.0)d,中位体重 5.0(4.1,6.4)kg。所有患者术前行超声心动图,48 例行 CT 造影,3 例行磁共振成像(MRI),并且术中确认了解剖形态。其中合并动脉导管未闭 17 例,室间隔缺损 1 例,气管狭窄 5 例,肺静脉梗阻 23 例。术前 5 例患者行呼吸机辅助呼吸。
根据患者的超声心动图、血管造影和外科手术的描述,按照 Chowdhury 等[3-4]的建议将它们分为 3 种不同类型:“3+1”型(3 支肺静脉回流入同一个部位,而另一支肺静脉回流另一侧部位);“2+2”型(两侧的肺静脉分别回流入不同的位置);怪异型(无法归入以上两类的怪异解剖类型)。“3+1”型患者共 38 例,其中男 27 例、女 11 例,中位年龄 98.5(53.8,184.8)d,中位体重 5.1(4.2,6.1)kg;“2+2”型患者共 9 例,其中男 5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114.0(73.0,237.5)d,中位体重 5.5(4.0,5.0)kg;怪异型患者共 4 例,其中男 3 例、女 1 例,中位年龄 133.0(40.0,1 074.3)d,中位体重 4.4(3.5,11.9)kg;见表 1。
1.2 手术方法
患儿均在常规体外循环下进行手术,采用胸骨正中切口。4 例(7.8%)患者使用深低温停循环。心肌保护液使用冷晶体保护液。
“3+1”型 38 例。27 例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右上、下侧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冠状静脉窦去顶;房间隔缺损(ASD)补片修补(Van Praagh 或 Mee 法)。2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van Son 法,Berdat 法。1 例右上及右中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Warden 法,Berdat 法。1 例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右上、下侧肺静脉及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心上途径共干-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左下肺静脉与左心房吻合。1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Berdat 法。1 例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右上、下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到膈下,采用心尖提升到右侧胸膜腔,心后途径使用垂直静脉连续部分吻合共干-左心房。1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采用 van Son 法。1 例右上肺静脉分为多支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采用共干-左心房吻合,切断右上肺静脉和部分上腔静脉,上腔静脉-右心房吻合。1 例右上肺静脉分为多支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Berdat 法。1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中、下肺静脉及左上、下肺静脉回流到膈下,采用心尖提升到右侧胸膜腔,心后途径使用垂直静脉连续部分吻合共干-左心房,Berdat 法连接右上肺静脉。1 例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分别回流入无名静脉及冠状静脉窦,右上、下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结扎垂直静脉-无名静脉连接处,冠状静脉窦去顶,所有肺静脉连接到左心房,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3+1”型术前和术后解剖形态分别见图 1a和图 1b。
 图1
术前术后解剖图像
图1
术前术后解剖图像
a:“3+1”型术前解剖图像,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右上、下侧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b:“3+1”型术后解剖图像;c:“2+2”型术前解剖图像,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左上、中、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d:“2+2”型术后解剖图像;LSPV:左上肺静脉;LMPV:左中肺静脉;LIPV:左下肺静脉;RSPV:右上肺静脉;RIPV:右下肺静脉;RPV:右肺静脉;VV:垂直静脉;IV:无名静脉;RA:右心房
“2+2”型 9 例。4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左上及左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冠状静脉窦去顶,右肺静脉与左心房连接,横断垂直静脉与左心耳吻合,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下腔静脉,采用 Berdat 法,共干-左心房吻合,保持垂直静脉开放。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左上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Berdat 法。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左上、中、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冠状静脉窦去顶,右肺静脉连接到左心房,横断垂直静脉与左心耳吻合,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侧上腔静脉,左上及左下肺静脉经左侧上腔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右侧共汇-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结扎左侧上腔静脉和右肺静脉。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及左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门静脉,采用 Warden 方法。“2+2”型术前和术后解剖形态分别见图 1c 和图 1d。
怪异型 4 例。2 例 4 支肺静脉汇合成共干后,随后分别回流入冠状静脉窦以及无名静脉,采用结扎垂直静脉和冠状静脉窦,共干-左心房吻合,ASD 补片修补。1 例右上、下肺静脉,左下肺静脉以及 1 支左上肺静脉分支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另一支左上肺静脉分支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垂直静脉-无名静脉连接处横断与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ASD 补片修补。1 例右上、下肺静脉、左上肺静脉以及一支左下肺静脉分支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另一支左下肺静脉分支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结扎垂直静脉,共干-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ASD 补片修补。
1.3 评价指标
急诊手术为入院后 24 h 内进行的手术,择期手术为入院后 24 h 以后进行的手术。术前肺静脉梗阻通过氧饱和度、超声心动图(流速>1.8 m/s 或 ASD<3 mm)和术前 CT 造影评估,并通过手术确认。术后肺静脉梗阻定义为超声心动图示吻合口或肺静脉流速>1.8 m/s[5]。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本研究中所有计量资料均为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及上下四分位数[ 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术后肺静脉梗阻情况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并使用 log-rank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Cox 回归模型分析术后肺静脉梗阻的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SCMCIRB-W2019017。
2 结果
2.1 早期结果
在性别、年龄、体重、术前肺静脉梗阻、术前处理、是否急诊等方面,3 种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无院内死亡发生。3 种类型延迟关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两两之间比较未发现明显差异。在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深低温停循环、机械通气时间、住 ICU 时间、住院时间、膈肌麻痹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随访结果
患者随访率为 96.1%,随访时间范围为 1~159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41.0(18.0,86.5)个月。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10 例患儿术后发生肺静脉梗阻,其中“3+1”型 7 例、“2+2”型 3 例,怪异型未发生术后肺静脉梗阻,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67)。发生术后肺静脉梗阻的患儿中有 2 例“3+1”型患儿再次手术,其中 1 例手术效果不佳,发生复发性再狭窄。
以术后肺静脉梗阻为终点绘出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9);见图 2。Cox 分析发现术前肺静脉梗阻与术后肺静脉梗阻明显相关(P=0.024);见表 3。
 图2
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的 Kaplan-Meier 曲线
图2
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的 Kaplan-Meier 曲线
3 讨论
混合型 TAPVC 十分罕见,其形态结构具有广泛的变异性,要求针对不同的解剖结构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因此精确的术前解剖学诊断对手术规划至关重要[3-4, 6-7]。超声心动图是首选的检查方法[8],可以比较准确地诊断混合型 TAPVC,然而由于混合型 TAPVC 的肺静脉形态多变,可能会产生误诊。由于声窗的限制,空间分辨率不足,可能会错误地诊断肺静脉的引流部位,尤其是膈下的引流部位和梗阻。因此一般需要计算机断层扫描准确地显示出肺静脉的形态、走行和梗阻是否存在,这样可以与超声的检查结果进行互补[9]。MRI 没有辐射,然而它需要屏气、镇静和较长的扫描时间。导管插入术是一项有创检查,如果患者病情稳定,可以进行导管插入术,这样可以了解患者的肺动脉压力情况。
需要根据患者的解剖形态采用个体化手术方式。混合型 TAPVC 中最常见的是“3+1”型。在该类型中,3 支肺静脉引流到一个公共部位,还有一条孤立的肺静脉。孤立肺静脉的处理仍存在争议。如果这支孤立的肺静脉发生阻塞,则要求与左心房连接,如果没有发生阻塞,则有多种处理方法。所有 4 支肺静脉完全重新连接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在新生儿中这支孤立的肺静脉比较细,直接吻合可能会导致术后狭窄。因此有人提出不修复这支孤立的肺静脉,然而这支孤立的肺静脉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可能造成远期肺静脉阻塞的风险。对患者密切随访时,这支孤立的肺静脉可以等长大到合适的尺寸进行二次手术纠正[10]。孤立肺静脉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切除对应的肺叶。肺叶切除后,肺组织随着年龄仍然可以生长。混合型 TAPVC 中第二种常见的是“2+2”型。在该类型中,每侧的两支肺静脉分别引流到一个公共部位。主要采用两侧分别吻合。
TAPVC 术后肺静脉阻塞发生率约为 10%~20%,与术后肺动脉高压和死亡密切相关[1-2]。TAPVC 术后肺静脉梗阻的机制尚不清楚。肺静脉梗阻的组织病理显示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酪氨酸激酶受体的激活、TGF-β 信号转导和血管紧张素Ⅱ途径可能参与其中[11]。本研究表明术前肺静脉梗阻是术后肺静脉梗阻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因为较小的肺静脉与左心房之间很难形成大的吻合口,从而引起术后肺静脉梗阻的进展[12]。其次,遗传因素可能在肺静脉梗阻中也起到了作用[13]。
本中心采用无内膜接触缝合技术(sutureless 技术)纠治 TAPVC 较晚,尚未应用在混合型 TAPVC 上。国外有研究[14]表明对于混合型 TAPVC,sutureless 技术效果良好。在本组患儿中,有 2 例“3+1”型再次手术,1 例采用补片扩大手术效果不佳,发生复发性再狭窄,1 例采用 sutureless 技术,未发生复发性再狭窄。sutureless 技术有以下优点:缝线不在肺静脉上从而减轻了肺静脉的增生反应;缝合线是简单的椭圆形,不会引起扭曲;该技术广泛适用于肺静脉的各种形态[15]。
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比较少。有一些梗阻性 TAPVC 患者可能在手术前就已经死亡。其次由于本研究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医疗技术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带来误差。患者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延迟诊断和手术。
综上所述,混合型 TAPVC 术前解剖形态多变,需要精确诊断和个体化手术方法。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温臣负责数据采集及初稿撰写;朱放负责文献检索;张茜、胡辰、陈浩负责患者随访及资料收集;仇黎生、施国丞、张浩负责内容指导;祝忠群、陈会文负责全文审校。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指全部肺静脉未能与左心房连接,其中混合型十分罕见,约占 10%[1]。手术修复 TAPVC 已取得良好效果,但是混合型手术后死亡和肺静脉梗阻的发生率仍然很高[2]。本文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06~2018 年手术矫正混合型 TAPVC 患者的效果,为该种罕见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手术治疗提供经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6~2018 年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行外科手术治疗混合型 TAPVC 患者(排除合并单心室、右心室双出口等患者)共 51 例,其中男 35 例、女 16 例,中位年龄 102.0(59.0,181.0)d,中位体重 5.0(4.1,6.4)kg。所有患者术前行超声心动图,48 例行 CT 造影,3 例行磁共振成像(MRI),并且术中确认了解剖形态。其中合并动脉导管未闭 17 例,室间隔缺损 1 例,气管狭窄 5 例,肺静脉梗阻 23 例。术前 5 例患者行呼吸机辅助呼吸。
根据患者的超声心动图、血管造影和外科手术的描述,按照 Chowdhury 等[3-4]的建议将它们分为 3 种不同类型:“3+1”型(3 支肺静脉回流入同一个部位,而另一支肺静脉回流另一侧部位);“2+2”型(两侧的肺静脉分别回流入不同的位置);怪异型(无法归入以上两类的怪异解剖类型)。“3+1”型患者共 38 例,其中男 27 例、女 11 例,中位年龄 98.5(53.8,184.8)d,中位体重 5.1(4.2,6.1)kg;“2+2”型患者共 9 例,其中男 5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114.0(73.0,237.5)d,中位体重 5.5(4.0,5.0)kg;怪异型患者共 4 例,其中男 3 例、女 1 例,中位年龄 133.0(40.0,1 074.3)d,中位体重 4.4(3.5,11.9)kg;见表 1。
1.2 手术方法
患儿均在常规体外循环下进行手术,采用胸骨正中切口。4 例(7.8%)患者使用深低温停循环。心肌保护液使用冷晶体保护液。
“3+1”型 38 例。27 例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右上、下侧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冠状静脉窦去顶;房间隔缺损(ASD)补片修补(Van Praagh 或 Mee 法)。2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van Son 法,Berdat 法。1 例右上及右中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Warden 法,Berdat 法。1 例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右上、下侧肺静脉及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心上途径共干-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左下肺静脉与左心房吻合。1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Berdat 法。1 例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右上、下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到膈下,采用心尖提升到右侧胸膜腔,心后途径使用垂直静脉连续部分吻合共干-左心房。1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采用 van Son 法。1 例右上肺静脉分为多支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采用共干-左心房吻合,切断右上肺静脉和部分上腔静脉,上腔静脉-右心房吻合。1 例右上肺静脉分为多支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下肺静脉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Berdat 法。1 例右上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中、下肺静脉及左上、下肺静脉回流到膈下,采用心尖提升到右侧胸膜腔,心后途径使用垂直静脉连续部分吻合共干-左心房,Berdat 法连接右上肺静脉。1 例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分别回流入无名静脉及冠状静脉窦,右上、下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结扎垂直静脉-无名静脉连接处,冠状静脉窦去顶,所有肺静脉连接到左心房,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3+1”型术前和术后解剖形态分别见图 1a和图 1b。
 图1
术前术后解剖图像
图1
术前术后解剖图像
a:“3+1”型术前解剖图像,左上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右上、下侧肺静脉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b:“3+1”型术后解剖图像;c:“2+2”型术前解剖图像,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左上、中、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d:“2+2”型术后解剖图像;LSPV:左上肺静脉;LMPV:左中肺静脉;LIPV:左下肺静脉;RSPV:右上肺静脉;RIPV:右下肺静脉;RPV:右肺静脉;VV:垂直静脉;IV:无名静脉;RA:右心房
“2+2”型 9 例。4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左上及左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冠状静脉窦去顶,右肺静脉与左心房连接,横断垂直静脉与左心耳吻合,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下腔静脉,采用 Berdat 法,共干-左心房吻合,保持垂直静脉开放。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右心房交界处,左上及左下肺静脉回流入右心房,采用 Berdat 法。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左上、中、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冠状静脉窦去顶,右肺静脉连接到左心房,横断垂直静脉与左心耳吻合,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右侧上腔静脉,左上及左下肺静脉经左侧上腔静脉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右侧共汇-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补片分隔共干和右心房,结扎左侧上腔静脉和右肺静脉。1 例右上及右下肺静脉回流入上腔静脉,左上及左下肺静脉经垂直静脉回流入门静脉,采用 Warden 方法。“2+2”型术前和术后解剖形态分别见图 1c 和图 1d。
怪异型 4 例。2 例 4 支肺静脉汇合成共干后,随后分别回流入冠状静脉窦以及无名静脉,采用结扎垂直静脉和冠状静脉窦,共干-左心房吻合,ASD 补片修补。1 例右上、下肺静脉,左下肺静脉以及 1 支左上肺静脉分支回流入冠状静脉窦,另一支左上肺静脉分支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采用垂直静脉-无名静脉连接处横断与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ASD 补片修补。1 例右上、下肺静脉、左上肺静脉以及一支左下肺静脉分支经垂直静脉回流入无名静脉,另一支左下肺静脉分支回流入冠状静脉窦,采用结扎垂直静脉,共干-左心房吻合;冠状静脉窦去顶,ASD 补片修补。
1.3 评价指标
急诊手术为入院后 24 h 内进行的手术,择期手术为入院后 24 h 以后进行的手术。术前肺静脉梗阻通过氧饱和度、超声心动图(流速>1.8 m/s 或 ASD<3 mm)和术前 CT 造影评估,并通过手术确认。术后肺静脉梗阻定义为超声心动图示吻合口或肺静脉流速>1.8 m/s[5]。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本研究中所有计量资料均为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及上下四分位数[ 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术后肺静脉梗阻情况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并使用 log-rank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Cox 回归模型分析术后肺静脉梗阻的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SCMCIRB-W2019017。
2 结果
2.1 早期结果
在性别、年龄、体重、术前肺静脉梗阻、术前处理、是否急诊等方面,3 种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无院内死亡发生。3 种类型延迟关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两两之间比较未发现明显差异。在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深低温停循环、机械通气时间、住 ICU 时间、住院时间、膈肌麻痹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随访结果
患者随访率为 96.1%,随访时间范围为 1~159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41.0(18.0,86.5)个月。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10 例患儿术后发生肺静脉梗阻,其中“3+1”型 7 例、“2+2”型 3 例,怪异型未发生术后肺静脉梗阻,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67)。发生术后肺静脉梗阻的患儿中有 2 例“3+1”型患儿再次手术,其中 1 例手术效果不佳,发生复发性再狭窄。
以术后肺静脉梗阻为终点绘出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9);见图 2。Cox 分析发现术前肺静脉梗阻与术后肺静脉梗阻明显相关(P=0.024);见表 3。
 图2
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的 Kaplan-Meier 曲线
图2
3 种类型术后肺静脉梗阻的 Kaplan-Meier 曲线
3 讨论
混合型 TAPVC 十分罕见,其形态结构具有广泛的变异性,要求针对不同的解剖结构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因此精确的术前解剖学诊断对手术规划至关重要[3-4, 6-7]。超声心动图是首选的检查方法[8],可以比较准确地诊断混合型 TAPVC,然而由于混合型 TAPVC 的肺静脉形态多变,可能会产生误诊。由于声窗的限制,空间分辨率不足,可能会错误地诊断肺静脉的引流部位,尤其是膈下的引流部位和梗阻。因此一般需要计算机断层扫描准确地显示出肺静脉的形态、走行和梗阻是否存在,这样可以与超声的检查结果进行互补[9]。MRI 没有辐射,然而它需要屏气、镇静和较长的扫描时间。导管插入术是一项有创检查,如果患者病情稳定,可以进行导管插入术,这样可以了解患者的肺动脉压力情况。
需要根据患者的解剖形态采用个体化手术方式。混合型 TAPVC 中最常见的是“3+1”型。在该类型中,3 支肺静脉引流到一个公共部位,还有一条孤立的肺静脉。孤立肺静脉的处理仍存在争议。如果这支孤立的肺静脉发生阻塞,则要求与左心房连接,如果没有发生阻塞,则有多种处理方法。所有 4 支肺静脉完全重新连接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在新生儿中这支孤立的肺静脉比较细,直接吻合可能会导致术后狭窄。因此有人提出不修复这支孤立的肺静脉,然而这支孤立的肺静脉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可能造成远期肺静脉阻塞的风险。对患者密切随访时,这支孤立的肺静脉可以等长大到合适的尺寸进行二次手术纠正[10]。孤立肺静脉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切除对应的肺叶。肺叶切除后,肺组织随着年龄仍然可以生长。混合型 TAPVC 中第二种常见的是“2+2”型。在该类型中,每侧的两支肺静脉分别引流到一个公共部位。主要采用两侧分别吻合。
TAPVC 术后肺静脉阻塞发生率约为 10%~20%,与术后肺动脉高压和死亡密切相关[1-2]。TAPVC 术后肺静脉梗阻的机制尚不清楚。肺静脉梗阻的组织病理显示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酪氨酸激酶受体的激活、TGF-β 信号转导和血管紧张素Ⅱ途径可能参与其中[11]。本研究表明术前肺静脉梗阻是术后肺静脉梗阻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因为较小的肺静脉与左心房之间很难形成大的吻合口,从而引起术后肺静脉梗阻的进展[12]。其次,遗传因素可能在肺静脉梗阻中也起到了作用[13]。
本中心采用无内膜接触缝合技术(sutureless 技术)纠治 TAPVC 较晚,尚未应用在混合型 TAPVC 上。国外有研究[14]表明对于混合型 TAPVC,sutureless 技术效果良好。在本组患儿中,有 2 例“3+1”型再次手术,1 例采用补片扩大手术效果不佳,发生复发性再狭窄,1 例采用 sutureless 技术,未发生复发性再狭窄。sutureless 技术有以下优点:缝线不在肺静脉上从而减轻了肺静脉的增生反应;缝合线是简单的椭圆形,不会引起扭曲;该技术广泛适用于肺静脉的各种形态[15]。
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比较少。有一些梗阻性 TAPVC 患者可能在手术前就已经死亡。其次由于本研究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医疗技术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带来误差。患者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延迟诊断和手术。
综上所述,混合型 TAPVC 术前解剖形态多变,需要精确诊断和个体化手术方法。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温臣负责数据采集及初稿撰写;朱放负责文献检索;张茜、胡辰、陈浩负责患者随访及资料收集;仇黎生、施国丞、张浩负责内容指导;祝忠群、陈会文负责全文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