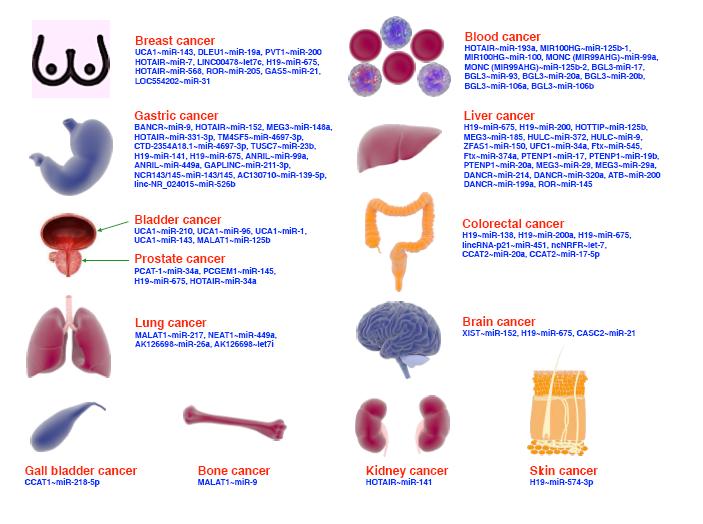引用本文: 段伊珊, 陈雨莎, 梁斌苗, 欧雪梅. 重症 H1N1 流感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的队列研究.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1, 20(5): 310-314. doi: 10.7507/1671-6205.202007050 复制
甲型流感是常见的人类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在流感病毒感染的背景下,没有免疫缺陷病史的宿主也可能发生曲霉的迅速侵袭[1-2]。侵袭性肺曲霉病(IPA)在重症流感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 19%[3]。因此 IPA 被认为是甲型流感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合并曲霉感染导致重症流感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升高[4-5]。合并 IPA 的重症流感患者死亡率为 40%~60%,远远高于合并其他感染或单纯的重症流感患者的死亡率[6]。我们之前的研究显示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为重症流感合并 IPA 患者中最常见的流感病毒亚型[7]。相较于其他季节性流感病毒,甲型 H1N1 病毒对呼吸道黏膜造成的损害更大。甲型 H1N1 病毒同时也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流感病毒亚型,深入探讨在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感染背景下合并 IPA 患者的危险因素和临床特征能够为早期识别那些合并 IPA 的高危患者、改善病死率提供依据。本研究共纳入了 2018 至 2019 年流感季华西医院收治的 114 例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其中合并 IPA 患者 64 例,全面分析重症 H1N1 合并 IPA 患者在基础疾病状况、起病症状、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改变特征、预后等方面的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患者 64 例,并选取同期住院的年龄及性别相匹配的单纯重症 H1N1 流感患者 50 例。排除既往有免疫缺陷病、肿瘤病史及年龄<18 岁的患者。重症流感的诊断标准:符合《2019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中重症或危重症诊断标准。IPA 的诊断标准:IPA 的诊断应包括宿主因素、临床特征和微生物学证据。流感被认为是 IPA 发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对于流感患者,IPA 的诊断往往不需要特定的宿主危险因素[8-9]。其中临床特征是指发热、呼吸困难、咯血、喘息等临床症状以及肺部影像学检查显示的新发病变。微生物学证据包括深部痰标本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曲霉培养阳性、血清或 BALF 的半乳糖甘露醇聚糖抗原(GM)检测阳性、肺组织标本病理学检查分离到曲霉。根据 EORTC/MSG 分级标准[10],将 IPA 患者分为三种诊断类型:确诊型 IPA、临床诊断型 IPA 和拟诊型 IPA。本组资料中的 64 例患者均属于临床诊断型 IPA。
1.2 方法
选取符合诊断标准的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患者,并按配对原则选取同期住院的单纯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建立两个队列。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信息、起病症状、实验室检查、微生物学资料(细菌、真菌及病毒检查)、胸部计算机体层摄影(CT)检查及预后相关指标[氧合指数、机械通气及气管插管比例、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入住比例及死亡率]。分析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的危险因素和临床特征。其中,连续使用 3 个月及以上的糖皮质激素界定为长期糖皮质激素使用;合并基础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肝肾功能不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血液疾病。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t 检验比较两组间数据的差别;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表示,t 检验比较两组间数据的差别;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一共纳入 114 例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其中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 50 例,平均年龄 60.5 岁;合并 IPA 组患者 64 例,平均年龄 57.5 岁。在患者年龄、性别、合并基础疾病类别、既往糖皮质激素使用几个方面的比较中,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1。
 )]
)]
2.2 临床症状
发热是重症流感患者最常见的症状。相较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合并 IPA 组患者出现发热和呼吸困难的比例更高,而咯血症状的比例更低。结果见表 2。
 )]
)]
2.3 实验室检查
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相比,合并 IPA 组患者入院时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均显著增高。合并 IPA 组患者的白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两组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计数均高于正常范围,CD4+ T 细胞计数的平均值均低于正常值,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2。
2.4 影像学改变
合并 IPA 组患者最常见的肺部影像表现依次为磨玻璃影改变、实变和结节。大多数患者多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影像学改变,根据新发病变分布范围、严重度选取其中一种作为主要影像学特征。分析后发现,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以磨玻璃影为主的比例明显更高,合并 IPA 组患者多在肺部磨玻璃影基础上合并实变和结节改变。其中结节改变在合并 IPA 组患者中比例明显增高,具有更多的特征性。结果见表 2。
2.5 微生物学检查
合并 IPA 组患者痰细菌培养结果最常见的细菌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杆菌是单纯重症 H1N1 患者最常见的三种细菌。其中,合并 IPA 组 42 例患者和单纯重症流感组 17 例患者完善了血液细菌培养检查。结果显示,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和合并 IPA 组两组患者血培养中最常见的细菌种类均为鲍曼不动杆菌。无论是血培养还是痰培养菌种分析,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2。
63 例合并 IPA 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完善了血清 GM 试验,其中 38 例患者(60.3%)结果显示为阳性。合并 IPA 组仅有 24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完善了 BALF 的 GM 试验,其中 23 例患者结果显示为阳性,阳性率高达 95.8%。此外,60 例合并 IPA 组患者完善了呼吸道标本真菌培养检查,阳性率为 61.7%。结果见表 2。
2.6 病情严重度及结局相关指标
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与合并 IPA 组患者间合并 Ⅰ 型呼吸衰竭比例、氧合指数组间比较均无明显差异。虽然合并 IPA 组患者需要有创呼吸支持和 ICU 入住比例远远高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合并 IPA 组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升高。结果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流感病毒感染背景下,曲霉感染的发生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以及 CD4+ T 细胞计数的降低无关,而是与和肺部过度炎症反应存在一定的关联。合并曲霉感染使得重症 H1N1 流感患者的死亡率由 32.0% 升至 51.6%。合并 IPA 的重症流感患者临床症状以发热和呼吸困难为主,肺部影像学改变多在磨玻璃影基础上合并实变和结节改变,其中合并结节改变具有一定特征性。
IPA 多发生在存在免疫缺陷的宿主中,但目前报道的大多数合并 IPA 的重症流感病例缺乏曲霉易感的宿主因素[1-5],流感本身被认为是曲霉感染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3-4, 11]。但在流感患者中继发曲霉感染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糖皮质激素常被应用在合并感染性休克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重症流感的治疗中,因此糖皮质激素的使用被认为是并发 IPA 的重要原因之一[12]。此外,也有小样本研究认为年龄、性别、基础疾病与重症流感患者并发 IPA 相关[4, 6, 13]。然而,本研究显示,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等与重症流感患者合并 IPA 无显著相关性。
流感病毒可能通过破坏支气管黏膜和减少黏液清除来促进曲霉的侵袭[14]。与季节性流感病毒相比,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对气道上皮细胞的损伤更大[15]。此外,病毒感染可激活炎症细胞,促发炎症介质瀑布样释放,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16]。与此同时,内源性抗炎症介质被释放入血以减少过度炎症介质释放引起的自身组织损伤,但过多的内源性抗炎症介质可以导致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CARS)[17]。SIRS 与 CARS 之间的失衡将导致细胞免疫功能的抑制,增加宿主对曲霉的易感性[18]。本研究观察到,相较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合并 IPA 患者的 CRP、IL-6 水平明显升高,往往合并更严重的炎症反应。IL-6 和 CRP 是流感病毒侵袭上皮细胞后合成和释放的具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可以激活一系列免疫反应和增强免疫细胞的吞噬作用,进而引起严重的组织和器官损害[16, 19]。IL-6 和 CRP 水平的显著上调提示了更为严重的临床表现、呼吸衰竭以及较差的预后[20-22]。病毒感染可以抑制机体细胞免疫功能进而引起 CD4+ T 细胞减少,因而也有小样本研究指出 CD4+ T 细胞的减少可能与流感患者曲霉易感性的增加相关[4, 13]。然而本研究显示在合并和不合并曲霉感染的重症甲型 H1N1 流感患者入院时均有 CD4+ T 细胞的减少,但两组患者间 CD4+ T 细胞降低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推测在无免疫缺陷病史的重症 H1N1 流感患者中,合并 IPA 的病理过程中占主导作用的是流感病毒感染所致肺部过度炎症反应和局部的免疫失调,而非全身的免疫功能障碍。
既往研究显示合并 IPA 的重症 H1N1 患者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如新月征、晕征)等[2, 23],这可导致 IPA 诊断和治疗的延迟以及后期死亡率增高。尽管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表现缺乏一定的特异性,但对于以发热和呼吸困难为起病症状,在磨玻璃影基础上合并结节为主要特征的影像改变的患者,我们应尽早主动完成曲霉相关的筛查,以达到早期诊断和改善预后的目的。此外,咯血通常在曲霉感染患者中更为常见,这是由于肺曲霉球的周围有丰富的血管网,曲霉球在空洞中内摩擦可损伤血管或者是局部侵入周围血管导致血管破裂从而引起空洞内出血咯血的情况。本研究显示合并 IPA 患者的影像学极少表现出血管侵袭的征象(包括空洞、晕征、新月征等),因而以咯血起病的患者并没有明显增多。
细菌感染作为重症流感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也被认为与合并曲霉感染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存在一定的关联[24]。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临床常见细菌感染指标(以入院时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PCT 水平为代表)均明显增加,但两组间并无明显差异。这表明,细菌感染是重症流感患者常见的继发感染类型,但其与是否合并曲霉感染并无确切关联。研究还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是合并曲霉感染的重症 H1N1 患者痰培养和血培养中最常见的细菌菌种,表明非发酵菌在合并 IPA 组中占主要位置,这对于我们治疗过程中抗生素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合并 IPA 可使得重症 H1N1 患者的病死率明显提高,同时需要有创呼吸支持和入住 ICU 的比例也有一定程度的升高。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是改善此类患者预后的关键。除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改变,本研究中患者 IPA 的诊断主要来源于血清和 BALF 真菌 GM 试验检查。尽管 BALF 的 GM 试验阳性率更高,但此类患者严重的呼吸衰竭和危重的病情限制了支气管镜检查的广泛开展,本组中合并 IPA 组也仅有 37.5% 的患者完成了 BALF 的 GM 试验检查。我们的数据显示,合并 IPA 的重症 H1N1 患者中血清 GM 试验阳性率为 60.3%,这远远高于既往研究 ICU 中 IPA 患者 33% 的血清 GM 试验阳性率[25]。因此,我们认为血清 GM 试验可作为怀疑合并曲霉感染的重症流感患者的主动监测方法。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重症 H1N1 流感患者中曲霉感染的发生与肺部过度的炎症反应有关,而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以及 CD4+ T 细胞计数无关。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并发曲霉感染可导致死亡率的显著升高。因此应该对高危患者主动积极地搜寻曲霉感染的微生物学证据(尤其是血清 GM 试验),避免误诊和漏诊。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甲型流感是常见的人类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在流感病毒感染的背景下,没有免疫缺陷病史的宿主也可能发生曲霉的迅速侵袭[1-2]。侵袭性肺曲霉病(IPA)在重症流感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 19%[3]。因此 IPA 被认为是甲型流感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合并曲霉感染导致重症流感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升高[4-5]。合并 IPA 的重症流感患者死亡率为 40%~60%,远远高于合并其他感染或单纯的重症流感患者的死亡率[6]。我们之前的研究显示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为重症流感合并 IPA 患者中最常见的流感病毒亚型[7]。相较于其他季节性流感病毒,甲型 H1N1 病毒对呼吸道黏膜造成的损害更大。甲型 H1N1 病毒同时也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流感病毒亚型,深入探讨在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感染背景下合并 IPA 患者的危险因素和临床特征能够为早期识别那些合并 IPA 的高危患者、改善病死率提供依据。本研究共纳入了 2018 至 2019 年流感季华西医院收治的 114 例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其中合并 IPA 患者 64 例,全面分析重症 H1N1 合并 IPA 患者在基础疾病状况、起病症状、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改变特征、预后等方面的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患者 64 例,并选取同期住院的年龄及性别相匹配的单纯重症 H1N1 流感患者 50 例。排除既往有免疫缺陷病、肿瘤病史及年龄<18 岁的患者。重症流感的诊断标准:符合《2019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中重症或危重症诊断标准。IPA 的诊断标准:IPA 的诊断应包括宿主因素、临床特征和微生物学证据。流感被认为是 IPA 发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对于流感患者,IPA 的诊断往往不需要特定的宿主危险因素[8-9]。其中临床特征是指发热、呼吸困难、咯血、喘息等临床症状以及肺部影像学检查显示的新发病变。微生物学证据包括深部痰标本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曲霉培养阳性、血清或 BALF 的半乳糖甘露醇聚糖抗原(GM)检测阳性、肺组织标本病理学检查分离到曲霉。根据 EORTC/MSG 分级标准[10],将 IPA 患者分为三种诊断类型:确诊型 IPA、临床诊断型 IPA 和拟诊型 IPA。本组资料中的 64 例患者均属于临床诊断型 IPA。
1.2 方法
选取符合诊断标准的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患者,并按配对原则选取同期住院的单纯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建立两个队列。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信息、起病症状、实验室检查、微生物学资料(细菌、真菌及病毒检查)、胸部计算机体层摄影(CT)检查及预后相关指标[氧合指数、机械通气及气管插管比例、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入住比例及死亡率]。分析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的危险因素和临床特征。其中,连续使用 3 个月及以上的糖皮质激素界定为长期糖皮质激素使用;合并基础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肝肾功能不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血液疾病。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t 检验比较两组间数据的差别;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表示,t 检验比较两组间数据的差别;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一共纳入 114 例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其中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 50 例,平均年龄 60.5 岁;合并 IPA 组患者 64 例,平均年龄 57.5 岁。在患者年龄、性别、合并基础疾病类别、既往糖皮质激素使用几个方面的比较中,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1。
 )]
)]
2.2 临床症状
发热是重症流感患者最常见的症状。相较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合并 IPA 组患者出现发热和呼吸困难的比例更高,而咯血症状的比例更低。结果见表 2。
 )]
)]
2.3 实验室检查
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相比,合并 IPA 组患者入院时血清 C 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均显著增高。合并 IPA 组患者的白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两组患者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计数均高于正常范围,CD4+ T 细胞计数的平均值均低于正常值,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2。
2.4 影像学改变
合并 IPA 组患者最常见的肺部影像表现依次为磨玻璃影改变、实变和结节。大多数患者多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影像学改变,根据新发病变分布范围、严重度选取其中一种作为主要影像学特征。分析后发现,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以磨玻璃影为主的比例明显更高,合并 IPA 组患者多在肺部磨玻璃影基础上合并实变和结节改变。其中结节改变在合并 IPA 组患者中比例明显增高,具有更多的特征性。结果见表 2。
2.5 微生物学检查
合并 IPA 组患者痰细菌培养结果最常见的细菌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杆菌是单纯重症 H1N1 患者最常见的三种细菌。其中,合并 IPA 组 42 例患者和单纯重症流感组 17 例患者完善了血液细菌培养检查。结果显示,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和合并 IPA 组两组患者血培养中最常见的细菌种类均为鲍曼不动杆菌。无论是血培养还是痰培养菌种分析,两组患者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2。
63 例合并 IPA 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完善了血清 GM 试验,其中 38 例患者(60.3%)结果显示为阳性。合并 IPA 组仅有 24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完善了 BALF 的 GM 试验,其中 23 例患者结果显示为阳性,阳性率高达 95.8%。此外,60 例合并 IPA 组患者完善了呼吸道标本真菌培养检查,阳性率为 61.7%。结果见表 2。
2.6 病情严重度及结局相关指标
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与合并 IPA 组患者间合并 Ⅰ 型呼吸衰竭比例、氧合指数组间比较均无明显差异。虽然合并 IPA 组患者需要有创呼吸支持和 ICU 入住比例远远高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组患者,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合并 IPA 组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升高。结果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流感病毒感染背景下,曲霉感染的发生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以及 CD4+ T 细胞计数的降低无关,而是与和肺部过度炎症反应存在一定的关联。合并曲霉感染使得重症 H1N1 流感患者的死亡率由 32.0% 升至 51.6%。合并 IPA 的重症流感患者临床症状以发热和呼吸困难为主,肺部影像学改变多在磨玻璃影基础上合并实变和结节改变,其中合并结节改变具有一定特征性。
IPA 多发生在存在免疫缺陷的宿主中,但目前报道的大多数合并 IPA 的重症流感病例缺乏曲霉易感的宿主因素[1-5],流感本身被认为是曲霉感染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3-4, 11]。但在流感患者中继发曲霉感染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糖皮质激素常被应用在合并感染性休克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重症流感的治疗中,因此糖皮质激素的使用被认为是并发 IPA 的重要原因之一[12]。此外,也有小样本研究认为年龄、性别、基础疾病与重症流感患者并发 IPA 相关[4, 6, 13]。然而,本研究显示,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等与重症流感患者合并 IPA 无显著相关性。
流感病毒可能通过破坏支气管黏膜和减少黏液清除来促进曲霉的侵袭[14]。与季节性流感病毒相比,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对气道上皮细胞的损伤更大[15]。此外,病毒感染可激活炎症细胞,促发炎症介质瀑布样释放,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16]。与此同时,内源性抗炎症介质被释放入血以减少过度炎症介质释放引起的自身组织损伤,但过多的内源性抗炎症介质可以导致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CARS)[17]。SIRS 与 CARS 之间的失衡将导致细胞免疫功能的抑制,增加宿主对曲霉的易感性[18]。本研究观察到,相较于单纯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合并 IPA 患者的 CRP、IL-6 水平明显升高,往往合并更严重的炎症反应。IL-6 和 CRP 是流感病毒侵袭上皮细胞后合成和释放的具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可以激活一系列免疫反应和增强免疫细胞的吞噬作用,进而引起严重的组织和器官损害[16, 19]。IL-6 和 CRP 水平的显著上调提示了更为严重的临床表现、呼吸衰竭以及较差的预后[20-22]。病毒感染可以抑制机体细胞免疫功能进而引起 CD4+ T 细胞减少,因而也有小样本研究指出 CD4+ T 细胞的减少可能与流感患者曲霉易感性的增加相关[4, 13]。然而本研究显示在合并和不合并曲霉感染的重症甲型 H1N1 流感患者入院时均有 CD4+ T 细胞的减少,但两组患者间 CD4+ T 细胞降低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推测在无免疫缺陷病史的重症 H1N1 流感患者中,合并 IPA 的病理过程中占主导作用的是流感病毒感染所致肺部过度炎症反应和局部的免疫失调,而非全身的免疫功能障碍。
既往研究显示合并 IPA 的重症 H1N1 患者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如新月征、晕征)等[2, 23],这可导致 IPA 诊断和治疗的延迟以及后期死亡率增高。尽管重症 H1N1 流感合并 IPA 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表现缺乏一定的特异性,但对于以发热和呼吸困难为起病症状,在磨玻璃影基础上合并结节为主要特征的影像改变的患者,我们应尽早主动完成曲霉相关的筛查,以达到早期诊断和改善预后的目的。此外,咯血通常在曲霉感染患者中更为常见,这是由于肺曲霉球的周围有丰富的血管网,曲霉球在空洞中内摩擦可损伤血管或者是局部侵入周围血管导致血管破裂从而引起空洞内出血咯血的情况。本研究显示合并 IPA 患者的影像学极少表现出血管侵袭的征象(包括空洞、晕征、新月征等),因而以咯血起病的患者并没有明显增多。
细菌感染作为重症流感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也被认为与合并曲霉感染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存在一定的关联[24]。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临床常见细菌感染指标(以入院时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PCT 水平为代表)均明显增加,但两组间并无明显差异。这表明,细菌感染是重症流感患者常见的继发感染类型,但其与是否合并曲霉感染并无确切关联。研究还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是合并曲霉感染的重症 H1N1 患者痰培养和血培养中最常见的细菌菌种,表明非发酵菌在合并 IPA 组中占主要位置,这对于我们治疗过程中抗生素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合并 IPA 可使得重症 H1N1 患者的病死率明显提高,同时需要有创呼吸支持和入住 ICU 的比例也有一定程度的升高。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是改善此类患者预后的关键。除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改变,本研究中患者 IPA 的诊断主要来源于血清和 BALF 真菌 GM 试验检查。尽管 BALF 的 GM 试验阳性率更高,但此类患者严重的呼吸衰竭和危重的病情限制了支气管镜检查的广泛开展,本组中合并 IPA 组也仅有 37.5% 的患者完成了 BALF 的 GM 试验检查。我们的数据显示,合并 IPA 的重症 H1N1 患者中血清 GM 试验阳性率为 60.3%,这远远高于既往研究 ICU 中 IPA 患者 33% 的血清 GM 试验阳性率[25]。因此,我们认为血清 GM 试验可作为怀疑合并曲霉感染的重症流感患者的主动监测方法。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重症 H1N1 流感患者中曲霉感染的发生与肺部过度的炎症反应有关,而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以及 CD4+ T 细胞计数无关。重症 H1N1 流感患者并发曲霉感染可导致死亡率的显著升高。因此应该对高危患者主动积极地搜寻曲霉感染的微生物学证据(尤其是血清 GM 试验),避免误诊和漏诊。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