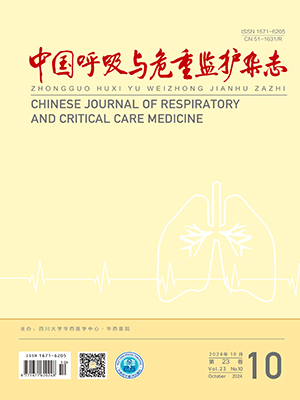引用本文: 张苏雅, 李梦丽, 王琴, 韩云. 血清尿素氮与肌酐比值预测重症肺炎患者病情与预后的价值.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1, 20(6): 408-415. doi: 10.7507/1671-6205.202103071 复制
重症肺炎又称中毒性肺炎或暴发性肺炎,是由各种病原体所致肺实质性炎症,具有严重感染中毒症状和相关并发症的肺炎。重症肺炎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中常见疾病,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情重、预后差等特点,除呼吸系统外,常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容易发生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属呼吸系统疾病中的急危重症。
虽然现代医学技术已取得明显进步,但重症肺炎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因此,积极寻找实用、快捷、灵敏的监测指标及方法,及时评价重症肺炎的预后,尽早调整治疗措施,降低病死率至关重要。国外研究发现,血清尿素氮与肌酐比值(UCR)与危重病的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以作为重症患者分解代谢的生物标志物[1],而高分解代谢可能是重症肺炎死亡的原因之一。目前 UCR 被认为是急性心力衰竭、COVID-19、血液透析患者[2-4]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尚未见将 UCR 用于评估重症肺炎患者病情与预后的相关文章报道。现将重症肺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 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病情与预后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来源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 日在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芳村分院、广州市慈善医院)ICU 住院期间诊断为重症肺炎的患者。本次研究经广东省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YE2020-218-01),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
1.2 病例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1)首先需符合社区获得性肺炎或医院获得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诊断标准[5-6],其次需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7];(2)年龄≥18 岁。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烧伤、库欣综合征、原发或继发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原发或继发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躁狂症、重症肌无力、恶性营养不良、急性大失血性疾病等,因上述疾病对机体分解代谢影响较大,为减少混杂因素影响,故予排除;(2)慢性肾脏病 3 期以上[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30 mL/(min·1.73 m2)]或入院血清肌酐>354 μmol/L、急性尿路梗阻、膀胱破裂;(3)肝硬化、亚急性肝衰竭和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的中期及晚期、入院血清总胆红素>10 倍正常值上限;(4)本次住院前及住院期间接受肾脏替代治疗;(5)数据缺失:缺少入院首次的肾功、血常规、血清炎症指标、PSI 评分与 APACHEⅡ评分所需参数等;(6)孕妇。研究期间多次住院的重复患者,选择最后一次住院数据为基线指标。
1.3 方法
1.3.1 分组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主要结局是住院期间的全因死亡率。根据本次住院结局分为生存组与死亡组。根据既往研究结果[8-1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可能影响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相关资料。(1)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肺炎分型、ICU 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等;(2)相关并发症:住院期间手术史、急性肝肾功能不全、ARDS、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急性加重、低蛋白血症、脓毒症、休克、MODS 等;(3)住院治疗措施:是否使用镇静镇痛、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时长等;(4)实验室检验结果(采集入院后首次):UC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细胞比容(HCT)、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D-二聚体(DD)等;(5)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入院当天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本研究承诺对所有患者资料均严格保密,并且不作任何商业用途。
1.3.2 观察指标
(1)比较生存组与死亡组患者一般资料、UCR、NLR、CRP、PCT、DD、APACHEⅡ评分、PSI 评分水平差异;(2)分析一般资料、并发症、住院治疗措施、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等与 UCR 水平的关系;(3)比较 UCR、NLR、CRP、PCT、DD、APACHEⅡ评分、PSI 评分各项指标对预后的价值;(4)对影响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研究设计为回顾性观察研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Independent-Sample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Q)]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Fisher 精确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的预测价值。将可能影响重症肺炎预后的因素纳入单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协变量后(向前:LR,P < 0.10)进行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Independent-Sample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Q)]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Fisher 精确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的预测价值。将可能影响重症肺炎预后的因素纳入单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协变量后(向前:LR,P < 0.10)进行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病例筛选流程见图 1。本研究共纳入 408 例患者,死亡组 88 例,生存组 320 例,病死率为 21.6%(88/408)。其中重症医院获得性肺炎(SHAP)病死率为 35.3%(24/68),高于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病死率(18.8%,64/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病例筛选流程图
图1
病例筛选流程图
两组年龄比较,死亡组患者年龄为 80(74~86)岁,大于生存组的 78(67~84)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性别、总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1。
2.2 住院病情与入院 UCR 的关系
2.2.1 人口资料与入院 UCR 的关系
重症肺炎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 U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大于 70 岁的重症肺炎患者 UCR 水平,高于 70 岁及以下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2.2.2 重症肺炎病情与入院 UCR 的关系
SCAP 与 SHAP 患者的 U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期间发生手术史、急性肝功能或肾功能不全、ARDS、呼吸衰竭、低蛋白血症、脓毒症、休克的重症肺炎患者,与未发生上述并发症的重症肺炎患者 U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期间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或 MODS 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高于未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MODS 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SI 3 级及以上的重症肺炎患者,或 APACHEⅡ评分大于 19 分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均分别高于 PSI 3 级以下或 APACHEⅡ评分不超过 19 分的重症肺炎,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CU 住院时间超过 10 d 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高于住院时间不超过 10 d 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2.2.3 治疗需求与入院 UCR 的关系
住院期间需行气管插管或需镇静镇痛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分别与未采用上述治疗手段的重症肺炎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机械通气时长超过 180 h 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高于机械通气时长不超过 180 h 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2.3 各项指标与预后的关系
死亡组 UCR 水平为 105.08(75.22~140.0),显著高于生存组的 86.66(62.66~106.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NLR、HCT、CRP、P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3。
 )]
)]
2.4 预后价值比较
NLR、HCT、CRP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均<0.5,无预测价值。P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AUC 虽为>0.5,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4。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AUC 为 0.648[95%CI(0.576~0.719)],其截断值为 108.74 时,敏感性为 47.7%,特异性为 77.8%,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图 2。
 图2
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
图2
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
2.5 重症肺炎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采用单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依次评估肺炎分型、年龄、慢阻肺急性加重、休克、MODS、ICU 住院时间、PSI 评级、机械通气时长和 UCR 等变量对重症肺炎死亡的影响,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P<0.05)纳入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结果发现 PSI 评级>3 级将增加重症肺炎死亡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4.297,95%CI 2.777~6.651,P<0.05);UCR>108.74 将增加重症肺炎死亡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545,95%CI 0.332~0.896,P<0.05)。结果见表 5。
3 讨论
重症肺炎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其确切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从本质上看,重症肺炎产生的全身炎症反应以及进而导致的 MODS,是机体免疫防御机制过度激活而引起自身破坏,以及高分解代谢状态加重机体能量消耗而引起内分泌紊乱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是细菌毒素直接损伤单一因素所致[11-12]。一项观察重大创伤患者生存曲线的研究发现[13],大部分患者虽然在创伤早期阶段得以存活,却死于继发的“晚期死亡高峰”,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与危重患者的高分解代谢状态有关。重症肺炎在起病初期高分解代谢状态已经发生,这种状态会导致新一轮临床问题的级联反应,或导致新发的器官衰竭或加重原有的器官衰竭,患者在短时间内会相继出现食欲下降、骨骼肌蛋白分解、糖异生增加、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紊乱,蛋白质消耗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使得患者本身的营养水平迅速下降,难以维持机体基本能量需求[14]。该项研究还对 UCR 值与肌肉横截面积(CSA)的相关性进行评估,结果提示 UCR 的增加与肌肉质量的逐渐丧失相一致,并发现 UCR 随着 ICU 住院时间延长和危重疾病进展而有明显不同,因此提出 UCR 是持续性危重病分解代谢的关键生物标志物。
UCR 作为机体分解代谢生物标志物的生理基础是十分坚实的。血尿素氮是由机体蛋白质及氨基酸代谢生成氨后通过肝脏水解生成并通过肾脏随尿排出,其值高低主要反映人体蛋白质的摄入与代谢、肝肾功能等生理反应,是衡量内源性蛋白质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动态过程的间接指标。血清肌酐是肌肉代谢的产物,其值高低与肌内肌酸浓度密切相关,肌肉质量的逐渐丧失导致肌酐的产生减少。高分解代谢状态下,机体会动员肌肉蛋白质分解,导致尿素氮升高,肌酐下降,尿素和肌酐的轨迹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UCR 升高可能是生物能量失效、蛋白稳态改变与肌肉持续消耗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UCR 值越高,则表示机体分解代谢状态越严重。为了使研究指标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本研究尽可能将所有可能影响尿素氮和肌酐水平的情况排除在本次研究外,并将住院期间合并急性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的 UCR 水平,与未合并急性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进行比较,发现无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 UCR 水平与年龄相关,大于 70 岁的重症肺炎患者 UCR 水平更高,这与年龄越大的患者营养状态越差、肌肉丢失情况越严重有关。在该研究中,重症肺炎患者住院期间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或 MODS 的 UCR 水平更高,因慢阻肺急性加重和 MODS 均为严重消耗性疾病,若同时合并重症肺炎,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炎症“瀑布效应”,严重损害机体免疫功能与营养状态[15-16],这种打击往往是致命性的。相关研究表明,合并慢阻肺或 MODS 是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7]。因此,临床上治疗重症肺炎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或是重症肺炎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时,除了积极抗感染外,应重视患者的营养与免疫支持力度。
该研究还发现 ICU 住院时间>10 d 和机械通气时长>180 h 的患者,UCR 水平更高。对于严格卧床的健康成人而言,肌力每天下降 1%,而在 ICU 中,采用机械通气、镇静镇痛的重症肺炎患者一般处于完全或近乎完全的制动状态,各种生理功能和营养状况均较差,严重影响肌蛋白的合成与分解平衡,更易出现肌肉衰弱[18]。另外,有创操作、谵妄状态等因素容易加重机体能量消耗[19]。据统计,重症肺炎患者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期间,并发营养不良现象高达 60%~80%[20],而营养不良会导致呼吸肌萎缩,影响呼吸功能的恢复及呼吸机的有效撤离,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甚至导致病死率增加。重症肺炎的高分解代谢状态使机体对氨基酸的合成代谢反应降低,导致肢体骨骼肌与肌肉质量下降,身体机能下降或肌肉力量下降,临床表现为体质量下降,四肢肌肉废用性萎缩与肌力下降,呼吸肌肌力下降,从而出现呼吸机依赖与脱机困难,自主咳嗽能力下降与反复误吸,四肢自主活动减少与卧床时间延长。且 ICU 住院时间超过 10 d 以上,其持续分解代谢的特征愈发突出[10],持续的高分解代谢会导致恶病质,严重损害宿主免疫功能,造成严重的肌肉萎缩和 ICU 相关性衰弱,最终导致重症肺炎患者住院时间延长,预后不佳甚至死亡。
目前国内常用 NLR、HCT、CRP、P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21-22],该研究将上述指标进行分析后发现,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组的 UCR 水平高于生存组,而其余指标分布水平在死亡组与生存组的差异并不明显。对重症肺炎患者预后评估方面,NLR、H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的预测特异性较高,但敏感性较低,可能导致临床对重症肺炎病情的严重程度判断滞后,延误治疗时机。而 CRP 为体内各种炎症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敏感性虽较高,但受干扰因素较多,创伤、应激、术后及任何感染性疾病都可引起 CRP 升高,因此其特异性较低,用其预测重症肺炎预后容易错误判断病情。临床观察发现,PCT 明显升高更多反映感染病灶来源于泌尿道、膀胱或肾脏,而肺部感染时 PCT 常常升高不明显甚至正常,这可能与 PCT 对肾小球系膜细胞具有直接毒性作用以及肾功能恶化时肾脏对 PCT 清除减少相关,也可能与老年重症肺炎患者 PCT 的产生延迟和释放受损,单一时间点 PCT 值无法反映肺部炎症的动态变化有关,从而使预测效能降低[23],因此其预测重症肺炎预后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均非最优。还有不少学者用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0 等炎症因子及 CD4+、CD8+ T 细胞计数等免疫分子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24-25],虽其敏感性与特异性均较好,但目前许多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仍难以普及。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AUC 为 0.648[95%CI(0.576~0.719)],其截断值为 108.74 时,敏感性为 47.7%,特异性为 77.8%,是相较于其他指标,敏感性和特异性综合较高的预后指标。研究提示,UCR>108.74 与 PSI>3 级是重症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UCR 是临床易获得、常反复检测、快捷、简便的指标,是重症肺炎患者分解代谢状态较为理想的临床标志物,易于在基层医院推广。故将 UCR 用于预测重症肺炎患者的病情与预后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设计方法是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多,资料收集难度较大,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可能存在偏倚和未知混杂因素。其次病例数量有限,样本量不够大。且研究指标需排除的干扰因素较多,其预测效能的外推性不够好。最后,该研究分析了危重病患者住院期间的病死率,未对生存患者出院后的结局进行随访,无法进行生存分析。因此,需要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证实其临床的实用价值。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重症肺炎又称中毒性肺炎或暴发性肺炎,是由各种病原体所致肺实质性炎症,具有严重感染中毒症状和相关并发症的肺炎。重症肺炎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中常见疾病,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情重、预后差等特点,除呼吸系统外,常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容易发生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属呼吸系统疾病中的急危重症。
虽然现代医学技术已取得明显进步,但重症肺炎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因此,积极寻找实用、快捷、灵敏的监测指标及方法,及时评价重症肺炎的预后,尽早调整治疗措施,降低病死率至关重要。国外研究发现,血清尿素氮与肌酐比值(UCR)与危重病的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以作为重症患者分解代谢的生物标志物[1],而高分解代谢可能是重症肺炎死亡的原因之一。目前 UCR 被认为是急性心力衰竭、COVID-19、血液透析患者[2-4]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尚未见将 UCR 用于评估重症肺炎患者病情与预后的相关文章报道。现将重症肺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 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病情与预后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来源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 日在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芳村分院、广州市慈善医院)ICU 住院期间诊断为重症肺炎的患者。本次研究经广东省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YE2020-218-01),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
1.2 病例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1)首先需符合社区获得性肺炎或医院获得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诊断标准[5-6],其次需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7];(2)年龄≥18 岁。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烧伤、库欣综合征、原发或继发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原发或继发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躁狂症、重症肌无力、恶性营养不良、急性大失血性疾病等,因上述疾病对机体分解代谢影响较大,为减少混杂因素影响,故予排除;(2)慢性肾脏病 3 期以上[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30 mL/(min·1.73 m2)]或入院血清肌酐>354 μmol/L、急性尿路梗阻、膀胱破裂;(3)肝硬化、亚急性肝衰竭和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的中期及晚期、入院血清总胆红素>10 倍正常值上限;(4)本次住院前及住院期间接受肾脏替代治疗;(5)数据缺失:缺少入院首次的肾功、血常规、血清炎症指标、PSI 评分与 APACHEⅡ评分所需参数等;(6)孕妇。研究期间多次住院的重复患者,选择最后一次住院数据为基线指标。
1.3 方法
1.3.1 分组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主要结局是住院期间的全因死亡率。根据本次住院结局分为生存组与死亡组。根据既往研究结果[8-1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可能影响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相关资料。(1)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肺炎分型、ICU 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等;(2)相关并发症:住院期间手术史、急性肝肾功能不全、ARDS、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急性加重、低蛋白血症、脓毒症、休克、MODS 等;(3)住院治疗措施:是否使用镇静镇痛、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时长等;(4)实验室检验结果(采集入院后首次):UC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细胞比容(HCT)、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D-二聚体(DD)等;(5)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入院当天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本研究承诺对所有患者资料均严格保密,并且不作任何商业用途。
1.3.2 观察指标
(1)比较生存组与死亡组患者一般资料、UCR、NLR、CRP、PCT、DD、APACHEⅡ评分、PSI 评分水平差异;(2)分析一般资料、并发症、住院治疗措施、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等与 UCR 水平的关系;(3)比较 UCR、NLR、CRP、PCT、DD、APACHEⅡ评分、PSI 评分各项指标对预后的价值;(4)对影响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研究设计为回顾性观察研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Independent-Sample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Q)]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Fisher 精确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的预测价值。将可能影响重症肺炎预后的因素纳入单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协变量后(向前:LR,P < 0.10)进行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Independent-Sample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Q)]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Fisher 精确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Jonckheere-Terpstra 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的预测价值。将可能影响重症肺炎预后的因素纳入单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协变量后(向前:LR,P < 0.10)进行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病例筛选流程见图 1。本研究共纳入 408 例患者,死亡组 88 例,生存组 320 例,病死率为 21.6%(88/408)。其中重症医院获得性肺炎(SHAP)病死率为 35.3%(24/68),高于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病死率(18.8%,64/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病例筛选流程图
图1
病例筛选流程图
两组年龄比较,死亡组患者年龄为 80(74~86)岁,大于生存组的 78(67~84)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性别、总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1。
2.2 住院病情与入院 UCR 的关系
2.2.1 人口资料与入院 UCR 的关系
重症肺炎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 U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大于 70 岁的重症肺炎患者 UCR 水平,高于 70 岁及以下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2.2.2 重症肺炎病情与入院 UCR 的关系
SCAP 与 SHAP 患者的 U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期间发生手术史、急性肝功能或肾功能不全、ARDS、呼吸衰竭、低蛋白血症、脓毒症、休克的重症肺炎患者,与未发生上述并发症的重症肺炎患者 U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期间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或 MODS 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高于未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MODS 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SI 3 级及以上的重症肺炎患者,或 APACHEⅡ评分大于 19 分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均分别高于 PSI 3 级以下或 APACHEⅡ评分不超过 19 分的重症肺炎,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CU 住院时间超过 10 d 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高于住院时间不超过 10 d 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2.2.3 治疗需求与入院 UCR 的关系
住院期间需行气管插管或需镇静镇痛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分别与未采用上述治疗手段的重症肺炎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机械通气时长超过 180 h 的重症肺炎患者的 UCR 水平,高于机械通气时长不超过 180 h 的重症肺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2。
2.3 各项指标与预后的关系
死亡组 UCR 水平为 105.08(75.22~140.0),显著高于生存组的 86.66(62.66~106.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NLR、HCT、CRP、P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3。
 )]
)]
2.4 预后价值比较
NLR、HCT、CRP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均<0.5,无预测价值。P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AUC 虽为>0.5,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4。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AUC 为 0.648[95%CI(0.576~0.719)],其截断值为 108.74 时,敏感性为 47.7%,特异性为 77.8%,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图 2。
 图2
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
图2
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 ROC 曲线
2.5 重症肺炎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采用单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依次评估肺炎分型、年龄、慢阻肺急性加重、休克、MODS、ICU 住院时间、PSI 评级、机械通气时长和 UCR 等变量对重症肺炎死亡的影响,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P<0.05)纳入多因素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结果发现 PSI 评级>3 级将增加重症肺炎死亡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4.297,95%CI 2.777~6.651,P<0.05);UCR>108.74 将增加重症肺炎死亡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545,95%CI 0.332~0.896,P<0.05)。结果见表 5。
3 讨论
重症肺炎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其确切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从本质上看,重症肺炎产生的全身炎症反应以及进而导致的 MODS,是机体免疫防御机制过度激活而引起自身破坏,以及高分解代谢状态加重机体能量消耗而引起内分泌紊乱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是细菌毒素直接损伤单一因素所致[11-12]。一项观察重大创伤患者生存曲线的研究发现[13],大部分患者虽然在创伤早期阶段得以存活,却死于继发的“晚期死亡高峰”,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与危重患者的高分解代谢状态有关。重症肺炎在起病初期高分解代谢状态已经发生,这种状态会导致新一轮临床问题的级联反应,或导致新发的器官衰竭或加重原有的器官衰竭,患者在短时间内会相继出现食欲下降、骨骼肌蛋白分解、糖异生增加、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紊乱,蛋白质消耗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使得患者本身的营养水平迅速下降,难以维持机体基本能量需求[14]。该项研究还对 UCR 值与肌肉横截面积(CSA)的相关性进行评估,结果提示 UCR 的增加与肌肉质量的逐渐丧失相一致,并发现 UCR 随着 ICU 住院时间延长和危重疾病进展而有明显不同,因此提出 UCR 是持续性危重病分解代谢的关键生物标志物。
UCR 作为机体分解代谢生物标志物的生理基础是十分坚实的。血尿素氮是由机体蛋白质及氨基酸代谢生成氨后通过肝脏水解生成并通过肾脏随尿排出,其值高低主要反映人体蛋白质的摄入与代谢、肝肾功能等生理反应,是衡量内源性蛋白质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动态过程的间接指标。血清肌酐是肌肉代谢的产物,其值高低与肌内肌酸浓度密切相关,肌肉质量的逐渐丧失导致肌酐的产生减少。高分解代谢状态下,机体会动员肌肉蛋白质分解,导致尿素氮升高,肌酐下降,尿素和肌酐的轨迹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UCR 升高可能是生物能量失效、蛋白稳态改变与肌肉持续消耗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UCR 值越高,则表示机体分解代谢状态越严重。为了使研究指标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本研究尽可能将所有可能影响尿素氮和肌酐水平的情况排除在本次研究外,并将住院期间合并急性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的 UCR 水平,与未合并急性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进行比较,发现无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 UCR 水平与年龄相关,大于 70 岁的重症肺炎患者 UCR 水平更高,这与年龄越大的患者营养状态越差、肌肉丢失情况越严重有关。在该研究中,重症肺炎患者住院期间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或 MODS 的 UCR 水平更高,因慢阻肺急性加重和 MODS 均为严重消耗性疾病,若同时合并重症肺炎,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炎症“瀑布效应”,严重损害机体免疫功能与营养状态[15-16],这种打击往往是致命性的。相关研究表明,合并慢阻肺或 MODS 是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7]。因此,临床上治疗重症肺炎合并慢阻肺急性加重,或是重症肺炎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时,除了积极抗感染外,应重视患者的营养与免疫支持力度。
该研究还发现 ICU 住院时间>10 d 和机械通气时长>180 h 的患者,UCR 水平更高。对于严格卧床的健康成人而言,肌力每天下降 1%,而在 ICU 中,采用机械通气、镇静镇痛的重症肺炎患者一般处于完全或近乎完全的制动状态,各种生理功能和营养状况均较差,严重影响肌蛋白的合成与分解平衡,更易出现肌肉衰弱[18]。另外,有创操作、谵妄状态等因素容易加重机体能量消耗[19]。据统计,重症肺炎患者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期间,并发营养不良现象高达 60%~80%[20],而营养不良会导致呼吸肌萎缩,影响呼吸功能的恢复及呼吸机的有效撤离,进而影响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甚至导致病死率增加。重症肺炎的高分解代谢状态使机体对氨基酸的合成代谢反应降低,导致肢体骨骼肌与肌肉质量下降,身体机能下降或肌肉力量下降,临床表现为体质量下降,四肢肌肉废用性萎缩与肌力下降,呼吸肌肌力下降,从而出现呼吸机依赖与脱机困难,自主咳嗽能力下降与反复误吸,四肢自主活动减少与卧床时间延长。且 ICU 住院时间超过 10 d 以上,其持续分解代谢的特征愈发突出[10],持续的高分解代谢会导致恶病质,严重损害宿主免疫功能,造成严重的肌肉萎缩和 ICU 相关性衰弱,最终导致重症肺炎患者住院时间延长,预后不佳甚至死亡。
目前国内常用 NLR、HCT、CRP、P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21-22],该研究将上述指标进行分析后发现,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组的 UCR 水平高于生存组,而其余指标分布水平在死亡组与生存组的差异并不明显。对重症肺炎患者预后评估方面,NLR、HCT、DD、PSI 评分、APACHEⅡ评分的预测特异性较高,但敏感性较低,可能导致临床对重症肺炎病情的严重程度判断滞后,延误治疗时机。而 CRP 为体内各种炎症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敏感性虽较高,但受干扰因素较多,创伤、应激、术后及任何感染性疾病都可引起 CRP 升高,因此其特异性较低,用其预测重症肺炎预后容易错误判断病情。临床观察发现,PCT 明显升高更多反映感染病灶来源于泌尿道、膀胱或肾脏,而肺部感染时 PCT 常常升高不明显甚至正常,这可能与 PCT 对肾小球系膜细胞具有直接毒性作用以及肾功能恶化时肾脏对 PCT 清除减少相关,也可能与老年重症肺炎患者 PCT 的产生延迟和释放受损,单一时间点 PCT 值无法反映肺部炎症的动态变化有关,从而使预测效能降低[23],因此其预测重症肺炎预后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均非最优。还有不少学者用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0 等炎症因子及 CD4+、CD8+ T 细胞计数等免疫分子预测重症肺炎患者预后[24-25],虽其敏感性与特异性均较好,但目前许多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仍难以普及。UCR 预测重症肺炎患者死亡的 AUC 为 0.648[95%CI(0.576~0.719)],其截断值为 108.74 时,敏感性为 47.7%,特异性为 77.8%,是相较于其他指标,敏感性和特异性综合较高的预后指标。研究提示,UCR>108.74 与 PSI>3 级是重症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UCR 是临床易获得、常反复检测、快捷、简便的指标,是重症肺炎患者分解代谢状态较为理想的临床标志物,易于在基层医院推广。故将 UCR 用于预测重症肺炎患者的病情与预后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设计方法是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受各种因素影响较多,资料收集难度较大,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可能存在偏倚和未知混杂因素。其次病例数量有限,样本量不够大。且研究指标需排除的干扰因素较多,其预测效能的外推性不够好。最后,该研究分析了危重病患者住院期间的病死率,未对生存患者出院后的结局进行随访,无法进行生存分析。因此,需要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证实其临床的实用价值。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