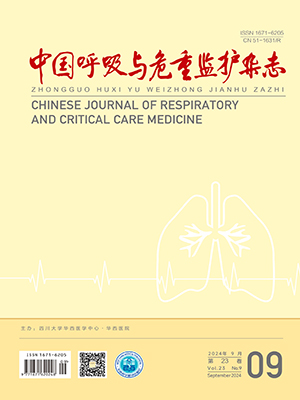引用本文: 邢子阳, 赵佳, 邓烈华, 张媛莉. 肌肉超声在机械通气患者撤机评估中的研究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4, 23(6): 442-446. doi: 10.7507/1671-6205.202309067 复制
机械通气是重症患者呼吸支持的重要手段之一,研究调查显示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中约有72%的机械通气的患者需要经历撤离机械通气[1],即撤机。如果撤机的时机把握错误,则可能会导致撤机失败或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对预后造成不良影响。撤机失败的病理生理学因素往往是复杂的[2-3],其中呼吸功能方面的影响常见于呼吸功能障碍[4],可以观察到患者呼吸肌肉数量、收缩力和质量的改变。尽管传统的指标可达到成功帮助大部分患者撤离机械通气,但缺乏对肌肉的功能状态的直观评估,或者需要依赖有创监测手段。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可以在床旁实现动态监测患者肌肉质量和功能的改变,适用于对重症患者的病情判断、评估,帮助医生制定出更为科学、准确的治疗方案[5]。近年来,有较多研究探讨使用肌肉超声来评估重症患者肌肉情况、预测拔管撤机时机及预后的价值。本文将就近年关于呼吸肌、辅助呼吸肌、外周骨骼肌超声结果对于机械通气患者的应用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呼吸肌
1.1 膈肌
膈肌是最重要的呼吸肌肉[6],在支撑总肺活量的作用中占比高达70%[7]。膈肌厚度(diaphragm thickness,DT)、膈肌增厚率(diaphragm thickening fraction,DTF)和膈肌移动度(diaphragmatic displacement,DD)是评价膈肌功能最常用的超声指标。在此基础上,近些年又提出一些新指标,如膈肌偏移-浅快呼吸指数(diaphragm 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D-RBSI)、膈肌增厚-浅快呼吸指数(diaphragm thickening 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DT-RSBI)以及膈肌回声密度等。
1.1.1 膈肌厚度、膈肌增厚率和膈肌移动度
DT是指膈肌在胸廓对合带处胸膜和腹膜之间的距离。在患者的吸气末和呼气末分别测得吸气末膈肌厚度和呼气末膈肌厚度。而有研究认为单纯测量膈肌厚度并不能识别膈肌功能障碍,因而衍生出DTF和DD的概念[8]。DTF可通过计算获得:DTF=(吸气末膈肌厚度–呼气末膈肌厚度)/呼气末膈肌厚度×100%[9-10],反映呼吸运动时膈肌厚度的变化及收缩功能。DD是指膈肌吸气末和呼气末之间的位移,反映呼吸时膈肌的运动。尽管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认为DTF和DD是不错的预测撤机的指标,但这两个指标预测撤机结果的准确性仍存在争议。一项2021年有关膈肌超声研究的Meta分析认为,DTF和DD作为预测撤机结果的指标,敏感性较低,特异性较高[11]。最近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发现,使用截止值时的可预测性为DTF>37%(敏感性80%,特异性52%)和DD>1.21 cm(敏感性94%,特异性71%)[12]。DTF和DD作为预测指标敏感性较高,特异性较低。不同研究得出DTF和DD预测撤机成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异质性,可能是因为阈值设置不一,也可能与这些试验的样本量、入组患者的基线特征、撤机失败标准不同有关,因此未来需要更多临床研究才能更好地总结出一个合适的DTF临界值,以用于提高撤机成功率。
1.1.2 膈肌位移-快速浅呼吸指数、膈肌增厚-浅快呼吸指数
快速浅呼吸指数(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RBSI)是呼吸频率与潮气量(tidal volume,VT)的比值,是预测撤机成功率最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13-14]。因此,Spadaro等[15]假设可以通过用DD代替VT联合RSBI评估超声结果,并将此指数命名为D-RSBI。结果发现当D-RSBI预测撤机成功的阈值为>1.3 r·min–1·mm–1,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64%,阳性预测值为57%,阴性预测值为95%,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D-RSBI、自主呼吸试验(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BT)、脓毒血症对撤机的影响,发现D-RSBI是与撤机失败独立相关的唯一预测因子。由此可见,在预测撤机结局时,D-RSBI指数比传统RSBI更准确。
DT-RSBI的产生类似于D-RSBI,在RSBI及DTF这些良好的预测撤机结果的指标基础上,张海翔等[16]提出用DTF替代VT得出另一个新指标,即DT-RSBI(DT-RSBI=呼吸频率/DTF)。他们发现DT-RSBI预测撤机成功的阈值为≥66次/min,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为0.87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8%和59%。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高DT-RSBI(优势比为1.06)是撤机成功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样,温亚东等[17]对108名机械通气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撤机成功组与失败组的DD、DTF以D-RSBI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膈肌的活动度在患者恢复自主呼吸中可能起关键作用,其中DT-RSBI预测撤机成功的阈值为27.9次/min,ROC曲线下面积为0.67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8%和59%。目前对DT-RSBI的研究仍较少,但就现有研究而言,与传统的RSBI相比较,膈肌超声相关指标DT-RSBI预测撤机成功率更为准确,或将成为指导撤机时机的良好指标。
1.1.3 膈肌回声密度
常规超声检查常用来评估肌肉厚度、肌肉增厚和缩短。近年来,有研究使用灰度分析来评估肌肉回声密度的变化[18]。根据超声信号反射的特性,健康的肌肉组织含有纤维组织较少,回声通常较低。而在一些疾病中,当脂肪和纤维组织替代肌肉,或者肌纤维变性和坏死,都会导致回声密度增加。回声密度增加或许与急性肌肉损伤、慢性肌病状态,以及危重患者的肌肉炎症、坏死和无力相关[19-20]。Coiffard等[21]通过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大部分机械通气患者的膈肌回声密度增加;其中相当大比例的患者在机械通气的早期就出现膈肌回声密度增加,并且表现出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具有一定相关性。另外,机械通气过程中膈肌厚度的增加和减小,回声密度都会显示增高。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厚度的减小是由于废用性萎缩,而膈肌厚度增加,往往提示膈肌超负荷引起损伤,这些变化与膈肌功能受损和不良临床结局密切相关,如果可以早期在回声强度上较好地体现出来,或许回声密度可以成为膈肌结构及功能早期变化的新型标志物,对于机械通气患者的预后评估存在一定临床价值。
当患者出现脱机困难或延迟脱机情况时,客观评价膈肌功能至关重要,撤机失败会引起一系列肺部并发症,早期发现并诊断膈肌功能障碍可避免后续撤机风险[22]。综合以上研究,膈肌超声有较多指标可以运用于预测危重症患者拔管失败风险,因此在排除患者原发疾病基础上,通过床边超声评估患者膈肌功能可有效预测撤机结果,也有学者提出机械通气患者撤机拔管前需常规行膈肌功能评估[23-24]。但是膈肌并不是唯一参与呼吸运动的呼吸肌,撤机也受到非膈肌相关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它出现损伤时,其他呼吸肌、辅助呼吸肌对于呼吸运动同样重要。有研究表明对于呼吸功能的评估,仅仅通过监测膈肌是片面的,应当结合其他肌肉的超声结果或传统指标,来进一步提高撤机的成功率[25]。
1.2 胸骨旁肋间肌
通过呼吸肌收缩能力评估或肌电图的使用,就可以实现床旁呼吸容量/负荷平衡的评估。基于此,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膈肌超声,因为可以使得膈肌及其功能可视化。然而,胸骨旁肋间肌在呼吸运动的同样至关重要。当膈肌功能障碍或呼吸负荷增加时,其他肌肉过度代偿,胸骨旁肋间肌作用就会强化[26-27],出现非生理性收缩(即增厚)的迹象。Dres等[28]报道,胸骨旁肋间肌增厚分数(parasternal intercostal muscle-thickening fraction,TFic)与机械通气患者的自发性呼吸试验的失败显著相关。另外,TFic在膈肌功能障碍患者中显著升高。具体来说,TFic超过8%的患者被认为存在膈肌功能障碍,TFic大于10%则可提示预测撤机失败可能。为了验证这一结果,Umbrello等[26]对膈肌和胸骨旁肋间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与膈肌功能障碍患者相比,膈肌功能正常患者的膈肌增厚分数更高(>30%),胸骨旁肋间肌的厚度分数更低(<5%)。在膈肌功能障碍的情况下,较低的膈肌增厚分数可能会导致吸气水平最低值升高,或膈外肌吸气水平最低值升高,这取决于机械通气呼吸机支持水平。在负荷-容量呼吸容量不平衡的情况下,胸骨旁肋间肌的超声结果或许有助于评估机械通气患者的吸气是否充足。由此可见,在膈肌障碍时,胸骨旁肋间肌的超声结果或许能更好体现呼吸功能改变,膈肌超声联合胸骨旁肋间肌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呼吸功能评估方法。
2 腹肌
在呼吸运动中,腹肌通常作为辅助呼吸肌发挥作用。在坐位和直立位的安静呼吸中,腹肌可出现紧张性收缩活动,增强膈肌的对位力,并优化其长度-张力关系,以产生压力。当通气负荷和微小通气增加时,它们也会出现增强膈肌性能的阶段性呼气活动。在呼气时腹肌收缩产生高呼气压力,有效地咳嗽和清除分泌物[29-31]。对腹肌作用的研究发现在撤机试验失败的患者中,腹肌对总呼吸肌力的辅助作用增加[32-33],其原因是机械通气时出现膈肌功能障碍,腹肌作为辅助肌可能会起作用,其功能对于患者耐受与急性呼吸衰竭相关的呼吸负荷的能力至关重要。
Schreiber等[34]通过观测咳嗽和呼气期间腹肌的厚度及腹肌的增厚分数(thickening fraction of abdominal muscles,TFabs),来探讨有关腹肌在呼吸运动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在健康受试者中,内斜肌和腹直肌增厚分数与呼气时产生的压力相关。在SBT失败的患者中,腹横肌和内斜肌的增厚分数显著增加(较基线分别增加13.2%、7.2%);从健康受试者的咳嗽期间测得的TFabs的正常下限为127%。在11例咳嗽期间TFabs>127%的患者中,只有1例需要重新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咳嗽期间较低的TFabs与较高的撤机失败的风险密切相关,TFabs每减少10%,脱离呼吸机失败的几率增加2.1%。咳嗽期间测量的TFabs(ROC曲线下面积为82%)比进行SBT 5 min时测量的膈肌增厚分数(ROC曲线下面积为70%)对撤机失败的预测辨别能力更强。由此可见,超声检查中腹肌增厚与呼气努力产生的气道压力有关。在机械通气患者中,咳嗽期间腹肌增厚分数的减少与撤机失败的高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既往研究显示部分机械通气患者会出现膈肌萎缩、膈肌水肿,以及一些胸腹部手术患者的切口位置与膈肌测量位置重叠,皆可能对膈肌超声测量的准确性造成影响[35-36]。另一方面,因左侧膈肌窗较小,临床上多选用右侧膈肌超声窗,有些患者因原发疾病出现右侧膈肌麻痹时也会影响测量结果。此外,膈肌超声测量可以有效预测患者是否会通过撤机试验,但不能预测患者是否需要再次插管,因为后者可能取决于腹肌功能,而不是膈肌功能。因此,当患者因膈肌萎缩、膈肌水肿、胸腹部手术或是单侧膈肌麻痹等情况导致膈肌超声显象不清晰时,膈肌超声联合腹肌超声监测可以更好地预测撤机风险以及再插管的风险,这有助于评估拔管后是否需要呼吸支持。
3 外周骨骼肌
外周骨骼肌超声常用来诊断ICU获得性虚弱,ICU获得性虚弱是ICU病房常见的并发症,有多项系统性回顾研究表明ICU获得性虚弱增加患者肺部感染风险,加重呼吸衰竭,延长机械通气时间[37-38]。外周骨骼肌肉虽然未在呼吸运动中直接发挥作用,但外周骨肌肌肉质量往往反映全身肌肉质量的变化,与机械通气患者通气时长和预后存在间接联系。
股四头肌作为外周骨骼肌,在健康状态下对于身体活动很重要,与其他肌肉群相比,它在急性和慢性疾病期间更容易萎缩,如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股直肌质量已被证明较低,并且与肺功能较差[39]、体力活动减少和更严重的疾病[40]具有一定相关性。目前对于外周骨骼肌的研究主要在于下肢肌肉,特别是股四头肌,Er等[41]在一项预测撤离机械通气时机的研究发现其中撤机失败组的体重指数中位数和股直肌+股中间肌的厚度值较低,临床虚弱评分、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和医院病死率较高;而股直肌+股中间肌的厚度临界值为21 mm时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为0.710,敏感性为82%,特异性为57%。他们认为早期超声测量的股直肌+股中间肌的厚度值是机械通气患者撤机成功的良好预测指标。除了常规肌骨超声监测方法,Mayer等[42]认为肌肉回声强度对外周骨骼肌肌肉质量的评估有更大的价值,他们发现第7天患者股直肌和胫前肌的肌肉厚度和横截面积以及肌力比基线值低,而回声强度增大,并且与ICU获得性虚弱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股直肌回声强度的变化是诊断ICU获得性虚弱的最强预测因子,ROC曲线下面积为0.912。由于股四头肌回声密度随时间增加与股四头肌活检的炎症和肌坏死相关,回声密度增加也许可以提示患者肌肉质量下降,导致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延长。
撤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ICU中可受到呼吸和心功能障碍、神经肌肉异常、肌肉力量下降和营养不良等情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外周骨骼肌质量和结构改变可以更好地反映机械通气患者营养不良和虚弱状态,或许可以作为评估撤机时机的手段。未来除了常规指标外,应当关注肌肉的回声密度的应用,探索其与全身肌肉的质量和呼吸功能改变的联系,但回声强度受到炎症、感染以及液体的变化影响[43],进而表现出肌肉的不均匀性,肌肉回声的变化及其与组织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仍有待确定。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定义肌肉和肌肉生成力之间的相关性。
4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用于预测患者机械通气撤离时机的传统指标有很多,在ICU病房中使用存在较多限制,特别是部分语言沟通障碍患者。肌肉超声评估在预测机械通气患者的拔管结果和预后评估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尽管目前准确性仍有待提高。呼吸肌、辅助呼吸肌、外周骨骼肌传统超声监测以及应用新型超声技术评估呼吸功能,可能为肌肉超声预测拔管结果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近年来的临床研究可能使该技术能够改进撤机的临床实践标准,并成为预测撤机时机的可靠手段。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机械通气是重症患者呼吸支持的重要手段之一,研究调查显示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中约有72%的机械通气的患者需要经历撤离机械通气[1],即撤机。如果撤机的时机把握错误,则可能会导致撤机失败或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对预后造成不良影响。撤机失败的病理生理学因素往往是复杂的[2-3],其中呼吸功能方面的影响常见于呼吸功能障碍[4],可以观察到患者呼吸肌肉数量、收缩力和质量的改变。尽管传统的指标可达到成功帮助大部分患者撤离机械通气,但缺乏对肌肉的功能状态的直观评估,或者需要依赖有创监测手段。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可以在床旁实现动态监测患者肌肉质量和功能的改变,适用于对重症患者的病情判断、评估,帮助医生制定出更为科学、准确的治疗方案[5]。近年来,有较多研究探讨使用肌肉超声来评估重症患者肌肉情况、预测拔管撤机时机及预后的价值。本文将就近年关于呼吸肌、辅助呼吸肌、外周骨骼肌超声结果对于机械通气患者的应用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呼吸肌
1.1 膈肌
膈肌是最重要的呼吸肌肉[6],在支撑总肺活量的作用中占比高达70%[7]。膈肌厚度(diaphragm thickness,DT)、膈肌增厚率(diaphragm thickening fraction,DTF)和膈肌移动度(diaphragmatic displacement,DD)是评价膈肌功能最常用的超声指标。在此基础上,近些年又提出一些新指标,如膈肌偏移-浅快呼吸指数(diaphragm 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D-RBSI)、膈肌增厚-浅快呼吸指数(diaphragm thickening 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DT-RSBI)以及膈肌回声密度等。
1.1.1 膈肌厚度、膈肌增厚率和膈肌移动度
DT是指膈肌在胸廓对合带处胸膜和腹膜之间的距离。在患者的吸气末和呼气末分别测得吸气末膈肌厚度和呼气末膈肌厚度。而有研究认为单纯测量膈肌厚度并不能识别膈肌功能障碍,因而衍生出DTF和DD的概念[8]。DTF可通过计算获得:DTF=(吸气末膈肌厚度–呼气末膈肌厚度)/呼气末膈肌厚度×100%[9-10],反映呼吸运动时膈肌厚度的变化及收缩功能。DD是指膈肌吸气末和呼气末之间的位移,反映呼吸时膈肌的运动。尽管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认为DTF和DD是不错的预测撤机的指标,但这两个指标预测撤机结果的准确性仍存在争议。一项2021年有关膈肌超声研究的Meta分析认为,DTF和DD作为预测撤机结果的指标,敏感性较低,特异性较高[11]。最近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发现,使用截止值时的可预测性为DTF>37%(敏感性80%,特异性52%)和DD>1.21 cm(敏感性94%,特异性71%)[12]。DTF和DD作为预测指标敏感性较高,特异性较低。不同研究得出DTF和DD预测撤机成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异质性,可能是因为阈值设置不一,也可能与这些试验的样本量、入组患者的基线特征、撤机失败标准不同有关,因此未来需要更多临床研究才能更好地总结出一个合适的DTF临界值,以用于提高撤机成功率。
1.1.2 膈肌位移-快速浅呼吸指数、膈肌增厚-浅快呼吸指数
快速浅呼吸指数(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RBSI)是呼吸频率与潮气量(tidal volume,VT)的比值,是预测撤机成功率最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13-14]。因此,Spadaro等[15]假设可以通过用DD代替VT联合RSBI评估超声结果,并将此指数命名为D-RSBI。结果发现当D-RSBI预测撤机成功的阈值为>1.3 r·min–1·mm–1,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64%,阳性预测值为57%,阴性预测值为95%,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D-RSBI、自主呼吸试验(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BT)、脓毒血症对撤机的影响,发现D-RSBI是与撤机失败独立相关的唯一预测因子。由此可见,在预测撤机结局时,D-RSBI指数比传统RSBI更准确。
DT-RSBI的产生类似于D-RSBI,在RSBI及DTF这些良好的预测撤机结果的指标基础上,张海翔等[16]提出用DTF替代VT得出另一个新指标,即DT-RSBI(DT-RSBI=呼吸频率/DTF)。他们发现DT-RSBI预测撤机成功的阈值为≥66次/min,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为0.872,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8%和59%。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高DT-RSBI(优势比为1.06)是撤机成功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样,温亚东等[17]对108名机械通气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撤机成功组与失败组的DD、DTF以D-RSBI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膈肌的活动度在患者恢复自主呼吸中可能起关键作用,其中DT-RSBI预测撤机成功的阈值为27.9次/min,ROC曲线下面积为0.673,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8%和59%。目前对DT-RSBI的研究仍较少,但就现有研究而言,与传统的RSBI相比较,膈肌超声相关指标DT-RSBI预测撤机成功率更为准确,或将成为指导撤机时机的良好指标。
1.1.3 膈肌回声密度
常规超声检查常用来评估肌肉厚度、肌肉增厚和缩短。近年来,有研究使用灰度分析来评估肌肉回声密度的变化[18]。根据超声信号反射的特性,健康的肌肉组织含有纤维组织较少,回声通常较低。而在一些疾病中,当脂肪和纤维组织替代肌肉,或者肌纤维变性和坏死,都会导致回声密度增加。回声密度增加或许与急性肌肉损伤、慢性肌病状态,以及危重患者的肌肉炎症、坏死和无力相关[19-20]。Coiffard等[21]通过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与健康受试者相比,大部分机械通气患者的膈肌回声密度增加;其中相当大比例的患者在机械通气的早期就出现膈肌回声密度增加,并且表现出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具有一定相关性。另外,机械通气过程中膈肌厚度的增加和减小,回声密度都会显示增高。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厚度的减小是由于废用性萎缩,而膈肌厚度增加,往往提示膈肌超负荷引起损伤,这些变化与膈肌功能受损和不良临床结局密切相关,如果可以早期在回声强度上较好地体现出来,或许回声密度可以成为膈肌结构及功能早期变化的新型标志物,对于机械通气患者的预后评估存在一定临床价值。
当患者出现脱机困难或延迟脱机情况时,客观评价膈肌功能至关重要,撤机失败会引起一系列肺部并发症,早期发现并诊断膈肌功能障碍可避免后续撤机风险[22]。综合以上研究,膈肌超声有较多指标可以运用于预测危重症患者拔管失败风险,因此在排除患者原发疾病基础上,通过床边超声评估患者膈肌功能可有效预测撤机结果,也有学者提出机械通气患者撤机拔管前需常规行膈肌功能评估[23-24]。但是膈肌并不是唯一参与呼吸运动的呼吸肌,撤机也受到非膈肌相关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它出现损伤时,其他呼吸肌、辅助呼吸肌对于呼吸运动同样重要。有研究表明对于呼吸功能的评估,仅仅通过监测膈肌是片面的,应当结合其他肌肉的超声结果或传统指标,来进一步提高撤机的成功率[25]。
1.2 胸骨旁肋间肌
通过呼吸肌收缩能力评估或肌电图的使用,就可以实现床旁呼吸容量/负荷平衡的评估。基于此,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膈肌超声,因为可以使得膈肌及其功能可视化。然而,胸骨旁肋间肌在呼吸运动的同样至关重要。当膈肌功能障碍或呼吸负荷增加时,其他肌肉过度代偿,胸骨旁肋间肌作用就会强化[26-27],出现非生理性收缩(即增厚)的迹象。Dres等[28]报道,胸骨旁肋间肌增厚分数(parasternal intercostal muscle-thickening fraction,TFic)与机械通气患者的自发性呼吸试验的失败显著相关。另外,TFic在膈肌功能障碍患者中显著升高。具体来说,TFic超过8%的患者被认为存在膈肌功能障碍,TFic大于10%则可提示预测撤机失败可能。为了验证这一结果,Umbrello等[26]对膈肌和胸骨旁肋间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与膈肌功能障碍患者相比,膈肌功能正常患者的膈肌增厚分数更高(>30%),胸骨旁肋间肌的厚度分数更低(<5%)。在膈肌功能障碍的情况下,较低的膈肌增厚分数可能会导致吸气水平最低值升高,或膈外肌吸气水平最低值升高,这取决于机械通气呼吸机支持水平。在负荷-容量呼吸容量不平衡的情况下,胸骨旁肋间肌的超声结果或许有助于评估机械通气患者的吸气是否充足。由此可见,在膈肌障碍时,胸骨旁肋间肌的超声结果或许能更好体现呼吸功能改变,膈肌超声联合胸骨旁肋间肌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呼吸功能评估方法。
2 腹肌
在呼吸运动中,腹肌通常作为辅助呼吸肌发挥作用。在坐位和直立位的安静呼吸中,腹肌可出现紧张性收缩活动,增强膈肌的对位力,并优化其长度-张力关系,以产生压力。当通气负荷和微小通气增加时,它们也会出现增强膈肌性能的阶段性呼气活动。在呼气时腹肌收缩产生高呼气压力,有效地咳嗽和清除分泌物[29-31]。对腹肌作用的研究发现在撤机试验失败的患者中,腹肌对总呼吸肌力的辅助作用增加[32-33],其原因是机械通气时出现膈肌功能障碍,腹肌作为辅助肌可能会起作用,其功能对于患者耐受与急性呼吸衰竭相关的呼吸负荷的能力至关重要。
Schreiber等[34]通过观测咳嗽和呼气期间腹肌的厚度及腹肌的增厚分数(thickening fraction of abdominal muscles,TFabs),来探讨有关腹肌在呼吸运动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在健康受试者中,内斜肌和腹直肌增厚分数与呼气时产生的压力相关。在SBT失败的患者中,腹横肌和内斜肌的增厚分数显著增加(较基线分别增加13.2%、7.2%);从健康受试者的咳嗽期间测得的TFabs的正常下限为127%。在11例咳嗽期间TFabs>127%的患者中,只有1例需要重新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咳嗽期间较低的TFabs与较高的撤机失败的风险密切相关,TFabs每减少10%,脱离呼吸机失败的几率增加2.1%。咳嗽期间测量的TFabs(ROC曲线下面积为82%)比进行SBT 5 min时测量的膈肌增厚分数(ROC曲线下面积为70%)对撤机失败的预测辨别能力更强。由此可见,超声检查中腹肌增厚与呼气努力产生的气道压力有关。在机械通气患者中,咳嗽期间腹肌增厚分数的减少与撤机失败的高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既往研究显示部分机械通气患者会出现膈肌萎缩、膈肌水肿,以及一些胸腹部手术患者的切口位置与膈肌测量位置重叠,皆可能对膈肌超声测量的准确性造成影响[35-36]。另一方面,因左侧膈肌窗较小,临床上多选用右侧膈肌超声窗,有些患者因原发疾病出现右侧膈肌麻痹时也会影响测量结果。此外,膈肌超声测量可以有效预测患者是否会通过撤机试验,但不能预测患者是否需要再次插管,因为后者可能取决于腹肌功能,而不是膈肌功能。因此,当患者因膈肌萎缩、膈肌水肿、胸腹部手术或是单侧膈肌麻痹等情况导致膈肌超声显象不清晰时,膈肌超声联合腹肌超声监测可以更好地预测撤机风险以及再插管的风险,这有助于评估拔管后是否需要呼吸支持。
3 外周骨骼肌
外周骨骼肌超声常用来诊断ICU获得性虚弱,ICU获得性虚弱是ICU病房常见的并发症,有多项系统性回顾研究表明ICU获得性虚弱增加患者肺部感染风险,加重呼吸衰竭,延长机械通气时间[37-38]。外周骨骼肌肉虽然未在呼吸运动中直接发挥作用,但外周骨肌肌肉质量往往反映全身肌肉质量的变化,与机械通气患者通气时长和预后存在间接联系。
股四头肌作为外周骨骼肌,在健康状态下对于身体活动很重要,与其他肌肉群相比,它在急性和慢性疾病期间更容易萎缩,如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股直肌质量已被证明较低,并且与肺功能较差[39]、体力活动减少和更严重的疾病[40]具有一定相关性。目前对于外周骨骼肌的研究主要在于下肢肌肉,特别是股四头肌,Er等[41]在一项预测撤离机械通气时机的研究发现其中撤机失败组的体重指数中位数和股直肌+股中间肌的厚度值较低,临床虚弱评分、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和医院病死率较高;而股直肌+股中间肌的厚度临界值为21 mm时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为0.710,敏感性为82%,特异性为57%。他们认为早期超声测量的股直肌+股中间肌的厚度值是机械通气患者撤机成功的良好预测指标。除了常规肌骨超声监测方法,Mayer等[42]认为肌肉回声强度对外周骨骼肌肌肉质量的评估有更大的价值,他们发现第7天患者股直肌和胫前肌的肌肉厚度和横截面积以及肌力比基线值低,而回声强度增大,并且与ICU获得性虚弱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股直肌回声强度的变化是诊断ICU获得性虚弱的最强预测因子,ROC曲线下面积为0.912。由于股四头肌回声密度随时间增加与股四头肌活检的炎症和肌坏死相关,回声密度增加也许可以提示患者肌肉质量下降,导致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延长。
撤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ICU中可受到呼吸和心功能障碍、神经肌肉异常、肌肉力量下降和营养不良等情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外周骨骼肌质量和结构改变可以更好地反映机械通气患者营养不良和虚弱状态,或许可以作为评估撤机时机的手段。未来除了常规指标外,应当关注肌肉的回声密度的应用,探索其与全身肌肉的质量和呼吸功能改变的联系,但回声强度受到炎症、感染以及液体的变化影响[43],进而表现出肌肉的不均匀性,肌肉回声的变化及其与组织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仍有待确定。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定义肌肉和肌肉生成力之间的相关性。
4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用于预测患者机械通气撤离时机的传统指标有很多,在ICU病房中使用存在较多限制,特别是部分语言沟通障碍患者。肌肉超声评估在预测机械通气患者的拔管结果和预后评估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尽管目前准确性仍有待提高。呼吸肌、辅助呼吸肌、外周骨骼肌传统超声监测以及应用新型超声技术评估呼吸功能,可能为肌肉超声预测拔管结果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近年来的临床研究可能使该技术能够改进撤机的临床实践标准,并成为预测撤机时机的可靠手段。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