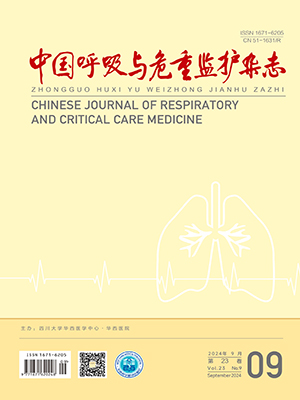引用本文: 郭丽, 王凯歌. 良恶性胸膜疾病影像学诊断进展.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4, 23(6): 437-441. doi: 10.7507/1671-6205.202311045 复制
胸膜疾病是内科常见病,包括气胸、胸腔积液、胸膜感染及肿瘤、胸膜钙化、粘连及增厚等。胸膜疾病常继发于其他疾病,亦可原发出现,产生相关症状和体征。胸膜疾病的病因诊断,尤其是良恶性鉴别诊断是临床诊疗中的重点和难点。近年发布的胸膜疾病诊疗指南或专家共识对胸腔穿刺、胸膜活检及内科胸腔镜等有创诊断方法进行详细总结论述[1-2]。作为无创诊断方法,胸部X线摄影(chest X radiography,CXR)、胸部超声(chest ultrasonography,CUS)、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影像学检查在胸膜疾病的病因诊断及良恶性鉴别诊断中亦具有重要作用。CXR或普通CT即可诊断气胸且无需良恶性鉴别,因此本文就不同影像学检查在除气胸外的各类胸膜疾病诊断及良恶性鉴别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胸腔积液
1.1 CXR
胸腔积液是指胸膜腔内积聚过多液体,常继发于肿瘤、结核或其他疾病[3-5]。CXR可发现200 mL以上的胸腔积液,但无法区分积液性质。CXR肋膈角变钝提示少量胸腔积液,约200~300 mL;正位CXR发现单侧胸腔中下部(约第4前肋水平)外高内低的弧形阴影提示中等量胸腔积液;CXR发现单侧胸腔透亮度减低,肺组织受压,上肺部分可见(约第2前肋水平),纵隔向对侧移位,横膈下移时提示大量胸腔积液;CXR发现局限性大小不等的圆形、椭圆形或半月形密度增高影,且不随体位变化而改变,需考虑包裹性胸腔积液。CXR诊断胸腔积液快速、简便,用于疾病筛查具有优势。基于CXR的计算机辅助智能像素分析可快速评价胸腔积液的大小和体积[6]。但CXR对少量胸腔积液漏诊率较高,对有临床症状但CXR阴性患者需结合CUS或胸部CT进一步明确诊断。
1.2 CUS
CUS可发现20 mL以内的胸腔积液,基于CUS图像构建数学模型可准确测算胸腔积液量[7-8]。不同CUS表现可协助鉴别胸腔积液性质。胸膜增厚和胸腔分隔常提示渗出液,均匀回声多提示胸腔积血或脓胸[9-10],但胸腔积液的回声特性不能有效鉴别渗出液和漏出液[11]。合并胸膜结节、胸膜增厚或脏器结构改变等多提示恶性胸腔积液[12]。B超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敏感性较低,超声造影可提高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确性,胸膜增厚强化和肺实变不均匀强化与恶性胸腔积液显著相关[13]。Kalkanis等[14]研究发现肋骨像素与胸腔积液像素的比值与胸水乳酸脱氢酶、细胞计数和酸碱度密切相关,可辅助鉴别胸腔积液性质。Ozgokce等[15]利用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鉴别胸腔积液性质,发现界值为2.52 m/s时,鉴别漏出液与渗出液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1.0%和76.5%。Jiang等[16]报道超声组织弹性成像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能力优于普通CUS,敏感性为83.64%,特异性为90.67%,而普通CUS的敏感性仅60.0%。CUS也可评估恶性胸腔积液行胸膜固定术的治疗效果。Corcoran等[17]按照是否存在“胸膜滑动征”分别记0、2分,不确定记为1分,在胸膜固定术前和术后对单侧胸腔9个区域进行评分,发现术后24 h评分高者胸腔固定成功率高。
1.3 胸部CT
胸部CT不仅显示胸腔积液的程度和部位,还可发现肺内、胸膜、膈肌、肺门和纵隔等部位的病变,有助于胸腔积液的病因诊断及良恶性鉴别[1]。相对于平扫,增强CT可更清楚显影异常增厚胸膜或结节,是胸部恶性肿瘤影像学诊断的金标准[18]。结节性胸膜增厚、不规则性胸膜增厚、纵隔胸膜增厚、壁层胸膜增厚>1 cm和环状胸膜增厚等CT影像学特征多提示恶性胸腔积液,诊断特异性为78%~100%,敏感性为36%~68% [1, 19]。既往报道胸部CT良恶性胸腔积液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差异较大,可能归因于纳入患者的胸部疾病谱不同,多以恶性胸膜间皮瘤为主。Lee等[3]报道结核性胸腔积液(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TPE)和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的CT鉴别要点:MPE的局灶性胸膜增厚数量更多、最大厚度更大、结节轮廓形态更多,而弥漫型和环周型胸膜增厚在TPE中更为常见;MPE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局灶性胸膜增厚数量>7个、最大厚度>6 mm、结节状轮廓并缺少弥漫性胸膜增厚,其中任意因素的MPE诊断敏感性为66%,特异性为92%。但是,单一胸部CT对MPE的诊断敏感性不高,易漏诊,胸部CT联合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使MPE的诊断敏感性达90%以上,特异性100%[20]。随着能量CT成像技术的发展,双能量CT结合多参数分析在良恶性胸腔积液诊断方面也表现出一定临床应用价值[21]。
Porcel等[22]基于胸部CT建立了区分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评分系统:胸膜病变(结节、肿块或增厚)≥1 cm(5分),肝转移瘤、腹部肿块或肺结节≥1 cm(各3分),无局限包裹性积液、心包积液或心脏扩大(各2分)。总分≥7分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4%和92%。但后续研究显示该评分系统单独应用并不能准确预测渗出性胸腔积液的良恶性,对临床决策参考价值不大[23]。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发展,利用AI构建深度学习模型在良恶性胸腔积液辅助诊断方面具有一定优势[24]。Wang等[25]基于胸部CT图像构建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外部验证集患者中的诊断敏感性为89.4%、特异性为65.1%,在胸腔积液良恶性鉴别诊断方面表现出良好性能。
1.4 胸部MRI
MRI用于直接诊断良恶性胸腔积液相关研究较少,对增强CT造影剂过敏患者或避免过量CT辐射的儿童有潜在应用价值。MRI扫及纵隔胸膜受累、环形胸膜增厚、结节状胸膜增厚、胸膜轮廓不规则、胸壁或膈肌浸润合并胸腔积液时多提示恶性疾病[1]。增强MRI使用造影剂可更好地评估胸膜病变,基础采集和注射造影剂后的延迟采集对比可有效协助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制定治疗计划以及评估治疗效果[26]。Rosmini等[27]利用心血管MR的T1 Mapping技术鉴别胸腔漏出液和渗出液,发现胸腔积液平扫T1值与蛋白含量呈负相关,T1 Mapping对胸腔渗出液的诊断敏感性为79%,特异性为89%,可有效避免对明确渗出液患者不必要的有创操作。Keskin等[28]发现胸腔渗出液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的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spersion coefficient,ADC)值显著低于漏出液,ADC阈值3.51×10–3mm2/s诊断胸腔渗出液的敏感性为90.4%,特异性为78%。
1.5 PET
PET是评估胸膜疾病的有效工具[29]。近年来,PET/CT的胸膜代谢和解剖显像广泛用于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尤其适用于对胸腔穿刺或胸膜活检等有创操作存在禁忌的患者,但PET/CT显像能否准确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存在争议[30]。PET/CT显像的分析方法一般包括视觉/定性分析、评分/分级系统或基于标准摄取值(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的半定量分析如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平均标准摄取值(SUVmean)及靶本比(target-to-background ratio,TBR)等[29-30]。既往研究报道基于PET/CT的各种分析方法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准确性差异较大。Porcel等[31]荟萃分析表明PET/CT融合显像半定量分析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为81%,特异性仅为74%。Sun等[32]荟萃分析发现PET/CT融合显像的视觉评估分析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为93.5%,显著高于CT和PET显像,诊断良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为92.6%。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可能是患者异质性及PET/CT显像评价指标选择不同所致。
Simsek等[33]研究表明利用PET/CT的单项指标均不能有效诊断良恶性胸腔积液,PE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1.3或PE SUVmax/MBP SUVmean>1.2联合弥漫性结节/结节性胸膜厚度、阻塞性肺不张、SUVmax>2.5的肺部结节或肿块、多发性肺结节中的至少一项,诊断MPE的敏感性为88.2%,特异性为100%;但PE SUVmax<1.3或PE SUVmax/MBP SUVmean<1.2且无其他表现并不能排除MPE。此外,Lu等[34]建立了基于PET/CT的评分模型,包括8个独立预测参数:胸膜结节或肿块(4分)、局灶性胸膜增厚(2分)、无胸膜腔(2分)、受累纵隔胸膜厚度≥0.5 cm(1分)、受累纵隔胸膜SUVmax≥3.0(1分)、受累非纵隔胸膜厚度≥0.5cm(1分)、受累非纵隔胸膜SUVmax≥3.0(1分)及胸腔积液SUVmax≥1.6(1分),该评分模型在验证集患者中诊断MPE的敏感性为91.7%、特异性为88.4%,评分0~2分的阴性预测值为99.4%,9~15分的阳性预测值为98.3%。其他研究报道PET/CT的评分模型和预测参数大同小异,除上述参数外,还包括癌胚抗原异常、淋巴结SUVmax以及肺部肿块/结节的SUVmax等,结果表明基于PET/CT的评分预测模型均能有效协助临床医师进行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35-37]。
MRI具有良好软组织分辨能力,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示正常胸膜结构和病变胸膜特征。因此,PET/MRI特有的代谢解剖成像在良恶性胸腔积液诊断方面有较好应用价值。彭文贝等[29]研究表明PET/MRI联合胸膜病变部位SUVmax和DWI特征对MPE的诊断敏感性75.6%、特异性100%;而PET/CT联合胸膜病变部位SUVmax和影像学特征对MPE的诊断敏感性85.4%、特异性83.3%。两者诊断MPE的曲线下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诊断效率相当。但PET/MRI对胸膜病灶显示更高的SUVmax和更高的TBR,并具有特异的胸膜DWI特征,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2 胸膜结节和肿块
胸膜结节和肿块包括良性胸膜疾病、原发性和转移性胸膜肿瘤等。CXR及超声对单纯性胸膜结节或肿块诊断价值有限。CT可清晰显示病变数目、大小及位置,协助判断胸膜病变的性质。钙化性病灶常提示良性,见于结核性胸膜炎后期钙化和石棉相关的胸膜斑。CT诊断胸膜斑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39%和79%,而以4.8为SUV临界值时,PET/CT诊断胸膜斑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1%和63%[38]。Lennartz等[39]研究显示能谱CT和传统CT诊断恶性胸膜疾病的敏感性分别为96%和83% ,特异性分别为84%和63%。因此,能谱CT可提高恶性胸膜肿瘤与非钙化良性胸膜病变的鉴别诊断准确性。
MRI扫描时间长、费用高,较少应用于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研究发现MRI对胸膜结核患者肺门淋巴结肿大、胸腔积液、肺空洞、结节及肺实变的检出率与胸部CT相当[40]。MRI较CT具有更好的软组织分辨率,特别是增强MRI。MRI发现纵隔胸膜受累、结节性或环形胸膜增厚(>1 cm)、胸壁及膈肌等邻近结构受累常提示恶性疾病[26]。
恶性胸膜间皮瘤(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MPM)和肺癌胸膜转移是两种最常见胸膜原发和转移肿瘤。MPM与长期石棉暴露相关,MPM胸部DWI的ADC值明显低于脓胸和胸腔积液[41],上皮细胞MPM的ADC值明显高于肉瘤样MPM。因此,DWI的ADC值被认为是MPM诊断的替代生物标志物[42]。远处转移将改变MPM的治疗方案,分期评估至关重要。全身MRI、PET/MRI、PET/CT对MPM的分期准确性均高于胸部增强CT[43];PET/MRI用于MPM的局部分期,比PET/CT更准确,尤其是T分期[44]。灌注加权MRI评估MPM的肿瘤体积比CT更快,重复性更好[45]。动态增强MRI可显示肿瘤血管化程度及预测MPM对化疗反应性及预后[46]。
肺癌胸膜转移对肺癌分期、治疗及预后至关重要。胸部CT是诊断肺癌胸膜转移的最常用方法,评价指标包括肿瘤大小、实性成分大小、肿瘤-胸膜夹角、肿瘤-胸膜距离和肿瘤-胸膜接触长度等[47]。研究报道胸部CT诊断肺癌胸膜转移的特异性约80.7%~99.2%,敏感性约25.0%~59.6%,准确性约70.8%~77%[48]。增强MRI扫描的T1梯度回波序列评估肺癌脏层胸膜侵犯时对肿瘤-胸膜接触长度、肿瘤-胸膜夹角以及拱距-最大肿瘤直径比的诊断性能与CT相同,但MRI优势在于能更加清晰地显示肿瘤-胸膜界面,有利于肺癌脏层胸膜表面侵犯的识别[49]。PET/MRI对直径小于3 cm的实性和亚实性肺腺癌胸膜转移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48]。
3 总结和展望
CXR、CUS、胸部CT、MRI和PET等影像学检查作为无创手段,在各类胸膜疾病的病因诊断尤其良恶性鉴别诊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IT实现对气胸高危患者的床旁持续监测,其在早期诊断气胸的准确性需进一步评价。能谱CT及DWI为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开辟新视角。PET与CT及MRI的融合图像不仅提高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能力,还可用于胸膜肿瘤分期及预测治疗反应。基于PET/CT及PET/MRI的良恶性胸膜疾病诊断新技术探索可能是未来研究热点。深度学习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影像学技术互相结合在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算法和指标的不断优化为提高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准确性、降低诊断时间和经济成本提供可能。但各类影像学检查在胸膜疾病的定性诊断方面存在局限,需结合胸腔穿刺或胸膜活检等有创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胸膜疾病是内科常见病,包括气胸、胸腔积液、胸膜感染及肿瘤、胸膜钙化、粘连及增厚等。胸膜疾病常继发于其他疾病,亦可原发出现,产生相关症状和体征。胸膜疾病的病因诊断,尤其是良恶性鉴别诊断是临床诊疗中的重点和难点。近年发布的胸膜疾病诊疗指南或专家共识对胸腔穿刺、胸膜活检及内科胸腔镜等有创诊断方法进行详细总结论述[1-2]。作为无创诊断方法,胸部X线摄影(chest X radiography,CXR)、胸部超声(chest ultrasonography,CUS)、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影像学检查在胸膜疾病的病因诊断及良恶性鉴别诊断中亦具有重要作用。CXR或普通CT即可诊断气胸且无需良恶性鉴别,因此本文就不同影像学检查在除气胸外的各类胸膜疾病诊断及良恶性鉴别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胸腔积液
1.1 CXR
胸腔积液是指胸膜腔内积聚过多液体,常继发于肿瘤、结核或其他疾病[3-5]。CXR可发现200 mL以上的胸腔积液,但无法区分积液性质。CXR肋膈角变钝提示少量胸腔积液,约200~300 mL;正位CXR发现单侧胸腔中下部(约第4前肋水平)外高内低的弧形阴影提示中等量胸腔积液;CXR发现单侧胸腔透亮度减低,肺组织受压,上肺部分可见(约第2前肋水平),纵隔向对侧移位,横膈下移时提示大量胸腔积液;CXR发现局限性大小不等的圆形、椭圆形或半月形密度增高影,且不随体位变化而改变,需考虑包裹性胸腔积液。CXR诊断胸腔积液快速、简便,用于疾病筛查具有优势。基于CXR的计算机辅助智能像素分析可快速评价胸腔积液的大小和体积[6]。但CXR对少量胸腔积液漏诊率较高,对有临床症状但CXR阴性患者需结合CUS或胸部CT进一步明确诊断。
1.2 CUS
CUS可发现20 mL以内的胸腔积液,基于CUS图像构建数学模型可准确测算胸腔积液量[7-8]。不同CUS表现可协助鉴别胸腔积液性质。胸膜增厚和胸腔分隔常提示渗出液,均匀回声多提示胸腔积血或脓胸[9-10],但胸腔积液的回声特性不能有效鉴别渗出液和漏出液[11]。合并胸膜结节、胸膜增厚或脏器结构改变等多提示恶性胸腔积液[12]。B超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敏感性较低,超声造影可提高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确性,胸膜增厚强化和肺实变不均匀强化与恶性胸腔积液显著相关[13]。Kalkanis等[14]研究发现肋骨像素与胸腔积液像素的比值与胸水乳酸脱氢酶、细胞计数和酸碱度密切相关,可辅助鉴别胸腔积液性质。Ozgokce等[15]利用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鉴别胸腔积液性质,发现界值为2.52 m/s时,鉴别漏出液与渗出液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1.0%和76.5%。Jiang等[16]报道超声组织弹性成像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能力优于普通CUS,敏感性为83.64%,特异性为90.67%,而普通CUS的敏感性仅60.0%。CUS也可评估恶性胸腔积液行胸膜固定术的治疗效果。Corcoran等[17]按照是否存在“胸膜滑动征”分别记0、2分,不确定记为1分,在胸膜固定术前和术后对单侧胸腔9个区域进行评分,发现术后24 h评分高者胸腔固定成功率高。
1.3 胸部CT
胸部CT不仅显示胸腔积液的程度和部位,还可发现肺内、胸膜、膈肌、肺门和纵隔等部位的病变,有助于胸腔积液的病因诊断及良恶性鉴别[1]。相对于平扫,增强CT可更清楚显影异常增厚胸膜或结节,是胸部恶性肿瘤影像学诊断的金标准[18]。结节性胸膜增厚、不规则性胸膜增厚、纵隔胸膜增厚、壁层胸膜增厚>1 cm和环状胸膜增厚等CT影像学特征多提示恶性胸腔积液,诊断特异性为78%~100%,敏感性为36%~68% [1, 19]。既往报道胸部CT良恶性胸腔积液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差异较大,可能归因于纳入患者的胸部疾病谱不同,多以恶性胸膜间皮瘤为主。Lee等[3]报道结核性胸腔积液(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TPE)和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的CT鉴别要点:MPE的局灶性胸膜增厚数量更多、最大厚度更大、结节轮廓形态更多,而弥漫型和环周型胸膜增厚在TPE中更为常见;MPE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局灶性胸膜增厚数量>7个、最大厚度>6 mm、结节状轮廓并缺少弥漫性胸膜增厚,其中任意因素的MPE诊断敏感性为66%,特异性为92%。但是,单一胸部CT对MPE的诊断敏感性不高,易漏诊,胸部CT联合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使MPE的诊断敏感性达90%以上,特异性100%[20]。随着能量CT成像技术的发展,双能量CT结合多参数分析在良恶性胸腔积液诊断方面也表现出一定临床应用价值[21]。
Porcel等[22]基于胸部CT建立了区分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评分系统:胸膜病变(结节、肿块或增厚)≥1 cm(5分),肝转移瘤、腹部肿块或肺结节≥1 cm(各3分),无局限包裹性积液、心包积液或心脏扩大(各2分)。总分≥7分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4%和92%。但后续研究显示该评分系统单独应用并不能准确预测渗出性胸腔积液的良恶性,对临床决策参考价值不大[23]。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发展,利用AI构建深度学习模型在良恶性胸腔积液辅助诊断方面具有一定优势[24]。Wang等[25]基于胸部CT图像构建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外部验证集患者中的诊断敏感性为89.4%、特异性为65.1%,在胸腔积液良恶性鉴别诊断方面表现出良好性能。
1.4 胸部MRI
MRI用于直接诊断良恶性胸腔积液相关研究较少,对增强CT造影剂过敏患者或避免过量CT辐射的儿童有潜在应用价值。MRI扫及纵隔胸膜受累、环形胸膜增厚、结节状胸膜增厚、胸膜轮廓不规则、胸壁或膈肌浸润合并胸腔积液时多提示恶性疾病[1]。增强MRI使用造影剂可更好地评估胸膜病变,基础采集和注射造影剂后的延迟采集对比可有效协助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制定治疗计划以及评估治疗效果[26]。Rosmini等[27]利用心血管MR的T1 Mapping技术鉴别胸腔漏出液和渗出液,发现胸腔积液平扫T1值与蛋白含量呈负相关,T1 Mapping对胸腔渗出液的诊断敏感性为79%,特异性为89%,可有效避免对明确渗出液患者不必要的有创操作。Keskin等[28]发现胸腔渗出液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的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spersion coefficient,ADC)值显著低于漏出液,ADC阈值3.51×10–3mm2/s诊断胸腔渗出液的敏感性为90.4%,特异性为78%。
1.5 PET
PET是评估胸膜疾病的有效工具[29]。近年来,PET/CT的胸膜代谢和解剖显像广泛用于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尤其适用于对胸腔穿刺或胸膜活检等有创操作存在禁忌的患者,但PET/CT显像能否准确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存在争议[30]。PET/CT显像的分析方法一般包括视觉/定性分析、评分/分级系统或基于标准摄取值(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的半定量分析如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平均标准摄取值(SUVmean)及靶本比(target-to-background ratio,TBR)等[29-30]。既往研究报道基于PET/CT的各种分析方法对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准确性差异较大。Porcel等[31]荟萃分析表明PET/CT融合显像半定量分析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为81%,特异性仅为74%。Sun等[32]荟萃分析发现PET/CT融合显像的视觉评估分析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为93.5%,显著高于CT和PET显像,诊断良性胸腔积液的敏感性为92.6%。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可能是患者异质性及PET/CT显像评价指标选择不同所致。
Simsek等[33]研究表明利用PET/CT的单项指标均不能有效诊断良恶性胸腔积液,PE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1.3或PE SUVmax/MBP SUVmean>1.2联合弥漫性结节/结节性胸膜厚度、阻塞性肺不张、SUVmax>2.5的肺部结节或肿块、多发性肺结节中的至少一项,诊断MPE的敏感性为88.2%,特异性为100%;但PE SUVmax<1.3或PE SUVmax/MBP SUVmean<1.2且无其他表现并不能排除MPE。此外,Lu等[34]建立了基于PET/CT的评分模型,包括8个独立预测参数:胸膜结节或肿块(4分)、局灶性胸膜增厚(2分)、无胸膜腔(2分)、受累纵隔胸膜厚度≥0.5 cm(1分)、受累纵隔胸膜SUVmax≥3.0(1分)、受累非纵隔胸膜厚度≥0.5cm(1分)、受累非纵隔胸膜SUVmax≥3.0(1分)及胸腔积液SUVmax≥1.6(1分),该评分模型在验证集患者中诊断MPE的敏感性为91.7%、特异性为88.4%,评分0~2分的阴性预测值为99.4%,9~15分的阳性预测值为98.3%。其他研究报道PET/CT的评分模型和预测参数大同小异,除上述参数外,还包括癌胚抗原异常、淋巴结SUVmax以及肺部肿块/结节的SUVmax等,结果表明基于PET/CT的评分预测模型均能有效协助临床医师进行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35-37]。
MRI具有良好软组织分辨能力,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示正常胸膜结构和病变胸膜特征。因此,PET/MRI特有的代谢解剖成像在良恶性胸腔积液诊断方面有较好应用价值。彭文贝等[29]研究表明PET/MRI联合胸膜病变部位SUVmax和DWI特征对MPE的诊断敏感性75.6%、特异性100%;而PET/CT联合胸膜病变部位SUVmax和影像学特征对MPE的诊断敏感性85.4%、特异性83.3%。两者诊断MPE的曲线下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诊断效率相当。但PET/MRI对胸膜病灶显示更高的SUVmax和更高的TBR,并具有特异的胸膜DWI特征,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2 胸膜结节和肿块
胸膜结节和肿块包括良性胸膜疾病、原发性和转移性胸膜肿瘤等。CXR及超声对单纯性胸膜结节或肿块诊断价值有限。CT可清晰显示病变数目、大小及位置,协助判断胸膜病变的性质。钙化性病灶常提示良性,见于结核性胸膜炎后期钙化和石棉相关的胸膜斑。CT诊断胸膜斑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39%和79%,而以4.8为SUV临界值时,PET/CT诊断胸膜斑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1%和63%[38]。Lennartz等[39]研究显示能谱CT和传统CT诊断恶性胸膜疾病的敏感性分别为96%和83% ,特异性分别为84%和63%。因此,能谱CT可提高恶性胸膜肿瘤与非钙化良性胸膜病变的鉴别诊断准确性。
MRI扫描时间长、费用高,较少应用于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研究发现MRI对胸膜结核患者肺门淋巴结肿大、胸腔积液、肺空洞、结节及肺实变的检出率与胸部CT相当[40]。MRI较CT具有更好的软组织分辨率,特别是增强MRI。MRI发现纵隔胸膜受累、结节性或环形胸膜增厚(>1 cm)、胸壁及膈肌等邻近结构受累常提示恶性疾病[26]。
恶性胸膜间皮瘤(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MPM)和肺癌胸膜转移是两种最常见胸膜原发和转移肿瘤。MPM与长期石棉暴露相关,MPM胸部DWI的ADC值明显低于脓胸和胸腔积液[41],上皮细胞MPM的ADC值明显高于肉瘤样MPM。因此,DWI的ADC值被认为是MPM诊断的替代生物标志物[42]。远处转移将改变MPM的治疗方案,分期评估至关重要。全身MRI、PET/MRI、PET/CT对MPM的分期准确性均高于胸部增强CT[43];PET/MRI用于MPM的局部分期,比PET/CT更准确,尤其是T分期[44]。灌注加权MRI评估MPM的肿瘤体积比CT更快,重复性更好[45]。动态增强MRI可显示肿瘤血管化程度及预测MPM对化疗反应性及预后[46]。
肺癌胸膜转移对肺癌分期、治疗及预后至关重要。胸部CT是诊断肺癌胸膜转移的最常用方法,评价指标包括肿瘤大小、实性成分大小、肿瘤-胸膜夹角、肿瘤-胸膜距离和肿瘤-胸膜接触长度等[47]。研究报道胸部CT诊断肺癌胸膜转移的特异性约80.7%~99.2%,敏感性约25.0%~59.6%,准确性约70.8%~77%[48]。增强MRI扫描的T1梯度回波序列评估肺癌脏层胸膜侵犯时对肿瘤-胸膜接触长度、肿瘤-胸膜夹角以及拱距-最大肿瘤直径比的诊断性能与CT相同,但MRI优势在于能更加清晰地显示肿瘤-胸膜界面,有利于肺癌脏层胸膜表面侵犯的识别[49]。PET/MRI对直径小于3 cm的实性和亚实性肺腺癌胸膜转移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48]。
3 总结和展望
CXR、CUS、胸部CT、MRI和PET等影像学检查作为无创手段,在各类胸膜疾病的病因诊断尤其良恶性鉴别诊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IT实现对气胸高危患者的床旁持续监测,其在早期诊断气胸的准确性需进一步评价。能谱CT及DWI为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开辟新视角。PET与CT及MRI的融合图像不仅提高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能力,还可用于胸膜肿瘤分期及预测治疗反应。基于PET/CT及PET/MRI的良恶性胸膜疾病诊断新技术探索可能是未来研究热点。深度学习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影像学技术互相结合在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算法和指标的不断优化为提高良恶性胸膜疾病的诊断准确性、降低诊断时间和经济成本提供可能。但各类影像学检查在胸膜疾病的定性诊断方面存在局限,需结合胸腔穿刺或胸膜活检等有创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