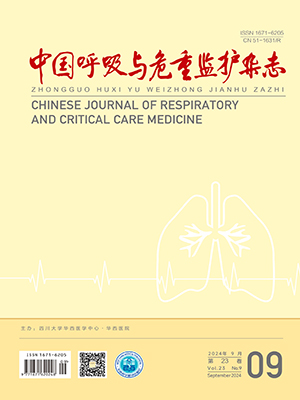引用本文: 赵艳丽, 易丹, 叶寰. 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相关急性致命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症一例报告.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4, 23(6): 434-436. doi: 10.7507/1671-6205.202311053 复制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72岁,因右下肺腺癌(cT3N0M1a Ⅳ期)、胸膜转移、肝转移、阻塞性肺炎入院化疗。入院完善检查,双上肢及双下肢行血管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次日行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术,即B超引导下于右上肢近肘部上臂3分之1贵要静脉处置入PICC导管,妥善固定,过程顺利,未见明显出血,右上肢肘横纹上10 cm测上臂臂围27 cm。并于PICC导管放置后第2天开始行第1程化疗,化疗方案为培美曲塞+顺铂+贝伐单抗。3天后化疗给药完成。
化疗结束后第2天,患者突然出现右上肢肿胀,未诉疼痛,查体右上肢水肿明显、皮温略高,右上肢肘横纹上10 cm测上臂臂围31 cm。考虑PICC相关急性上肢静脉血栓形成可能性大,推轮椅去B超室行上肢血管超声检查。B超显示右侧锁骨下静脉、腋静脉、贵要静脉血栓形成。患者返回病房途中突然诉胸闷、气促,随之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立即就近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组织抢救,测脉搏氧饱和度80%、心率106次/min、血压88/40 mm Hg(1 mm Hg=0.133 kPa)、呼吸30次/min,高度怀疑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立即给予多巴胺静脉注射升压,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仪给予氧浓度80%行呼吸支持,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抗凝。后患者神智逐渐转清,血压回升至103/62 mm Hg,脉搏氧饱和度升至92%,心率96次/min,呼吸26次/min。
病情相对平稳后转入我科呼吸ICU继续给予低分子肝素抗凝;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仪吸氧浓度60%,流量30 L/min呼吸支持;去甲肾上腺素升压行循环支持;右上肢制动,绝对卧床,定期测量臂围及患侧皮温变化。患者仍诉胸闷、气促。查血气分析提示:pH7.479,氧分压68.2 mm Hg,二氧化碳分压36.1 mm Hg,氧合指数113.6 mm Hg,动脉血乳酸1.6 mmol/L,查血D-二聚体18.635 mg/L,明显升高。心脏超声提示右心室扩大,肺动脉显示不清,未能测出肺动脉压力。次日,患者自觉症状明显缓解,右侧上臂臂围自31 cm降至28 cm,未吸氧状态下脉搏氧饱和度95%~97%,呼吸22次/min,停用去甲肾上腺素后血压120/75 mm Hg,心率60次/min。复查血气分析:pH7.432,氧分压79.80 mm Hg,二氧化碳分压39.5 mm Hg,氧合指数380 mm Hg,动脉血乳酸0.70 mmol/L。复查血D-二聚体7.496 mg/L,较前明显下降。
患者病情已趋平稳,遂前往CT室行CT肺动脉造影(CT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提示“左肺动脉主干末端、左上、左下肺动脉主干及部分分支、右上肺动脉前段分支内见低密度充盈缺损,考虑肺栓塞可能”(图1)。结合心脏超声右心扩大,以及患者急性起病,以意识丧失、低血压、低氧血症为主要表现,需要使用升压药才能纠正低血压等临床表现,根据2018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颁布的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患者符合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1]。因其右上肢深静脉系统沿PICC导管走行多发血栓形成,如强行拔除导管恐造成致命性肺栓塞,故保留该PICC导管继续维持患者化疗通道。根据该指南[1],继续给予患者低分子肝素抗凝,出院后改用利伐沙班继续抗凝治疗。2个月后复查CTPA显示“与前片示双侧肺动脉低密度充盈缺损,此次未见”(图2)。复查右上肢血管超声:原右上肢深静脉血栓均已消失。血栓脱落加重肺栓塞的风险已经消除,故拔除PICC导管,管端完整,未见血栓。请胸外科为其放置静脉输液岗,继续行抗肿瘤化疗治疗。
该病例没有溶栓主要考虑为以下几点:(1)患者使用了贝伐珠单抗这一抗血管生成药,有发生出血的风险;(2)患者年龄偏大,已经接近溶栓年龄高限;(3)在确诊肺栓塞之前的经验性抗凝治疗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氧合改善,右上肢因血栓引起的肿胀也明显消退。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抗凝治疗对患者相对安全,且患者血栓形成时间短,比较疏松;从临床表现来看,在抗凝治疗的基础上血栓已经开始自溶,再次发生致命性肺栓塞的风险较低,允许密切监测下继续抗凝治疗,如出现病情恶化的情况可随时进行溶栓治疗。后患者症状逐渐好转,故未行溶栓治疗。
该患者在放置PICC之前,曾行双下肢血管超声,未发现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在B超引导下行PICC置放术时,也未经超声发现右上肢静脉系统有血栓形成。此次肺血栓栓塞发生前曾出现明显的右上肢肿胀症状,后B超显示“右侧锁骨下静脉、腋静脉、贵要静脉血栓形成”而双下肢血管超声仍未发现血栓征象。此外,该患者本次入院未行PICC置入术时查D-二聚体正常,而在肺血栓栓塞当日其D-二聚体显著升高。由此可见其肺血栓栓塞的栓子来源应为右上肢深静脉血栓脱落,而右上肢深静脉血栓沿PICC导管走行形成,并在PICC导管置入后出现,故应与PICC导管置入有关,因此该患者应明确诊断为PICC相关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症。
2 讨论
PICC具有安全性强、留置时间长、减少穿刺的痛苦等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化疗,肠外营养,急危重症等治疗过程[2]。一项纳入美国密歇根州48家医院的76 242例住院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放置PICC的患者发生上肢近心端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为2.75/1 000患者日,下肢近心端深静脉血栓发生率1.04/1 000患者日,显著高于没有放置PICC的0.2/1 000患者日和0.44/1 000患者日。但在肺栓塞发生率方面,放置PICC的和非放置PICC分别为0.75/1 000患者日和0.44/1 000患者日,没有显著差异[3]。由此可见,PICC相关肺栓塞的发生率较低,而PICC相关高危肺栓塞就更为少见,查阅近年来文献尚未有相关报道。本例患者发生PICC相关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属于急性高危肺栓塞的一种类型,导致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低氧血症型呼吸衰竭、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才能纠正的低血压循环障碍,属于PICC相关致命性高危肺栓塞,虽然少见,但却极为凶险,临床上应给予高度重视。
本例为肺癌、化疗患者,属于PICC相关深静脉血栓的高风险人群[3-5]。此外,患者在化疗同时应用了抗血管生成药贝伐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正式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中明确写明该药存在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Howlett等[6]研究也发现在108例肺癌患者中应用贝伐珠单抗治疗,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患者达到了11例(10.2%),统计学分析显示有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风险比为2.39,95%置信区间1.29~4.42,P=0.006)。因此,本例患者同时存在肺癌、化疗、应用PICC以及应用抗血管生成药贝伐珠单抗等多个深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的叠加可能是导致该患者更早和更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甚至肺栓塞的重要原因。患者在放置PICC导管后5天即出现放置导管侧上肢深静脉多发血栓形成和高危肺栓塞,而以往也有报道肿瘤患者PICC相关血栓70%发生在置管后第1周,30%发生在置管后第2周[7]。由此可见,对于恶性肿瘤化疗的患者,放置PICC导管后需要更加密切地监测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尤其在置管后的2周内,如每日策上臂臂围、超声检查有无血栓形成、监测血D-二聚体等,一旦出现上肢肿胀、臂围增加,立即绝对卧床,患肢制动,进行床旁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如有血栓形成应立即进行抗凝治疗。
一项纳入64项研究共计29 503例患者的荟萃研究显示,PICC较中心静脉导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s,CVC)更容易发生上肢深静脉血栓,尤其是在重症患者和肿瘤患者中其上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更高。但PICC并不是引起肺栓塞的高危因素,也没有显著增加肺栓塞的发生率,且没有发生致命性肺栓塞的报道[8]。而另一项纳入75项研究共计10 9292例患者的荟萃研究也显示PICC较CVC更容易出现DVT,但在其中的随机对照研究却显示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9]。另一项关于86例CVC相关上肢深静脉血栓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在纳入的患者中13例发生了肺栓塞,其肺栓塞发病率高达15.1%,其中2例在使用了肝素抗凝治疗后仍死于肺栓塞,病死率2.3%[10]。可见PICC和CVC都是上肢深静脉血栓的高风险因素,但两者之间谁更容易引起血栓尚无定论。但CVC可能较PICC更容易发生致命性高危肺栓塞。我们推测CVC更容易发生致死性肺栓塞的原因是其穿刺和置管位置导致锁骨下静脉、股静脉和髂静脉等近心端粗大的深静脉有形成较大血栓的风险。而本例患者也被证实在锁骨下静脉形成了血栓,这可能是其发生致命性高危肺栓塞的重要原因。今后我们将更加关注PICC相关锁骨下静脉血栓形成与肺栓塞和高危肺栓塞发生的相关性,并做好发现锁骨下静脉血栓后肺栓塞的预防工作。
本例患者发生的事件说明PICC也可以引起致命性高危肺栓塞,虽然少见,但却是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一旦抢救不及时,很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对该类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有必要进行有效预防。但有研究显示预防性抗凝并没有减少PICC相关血栓发生率[9,11]。因此,PICC术后密切监测血栓发生情况显得尤为重要,如上肢臂围监测、血D-二聚体监测等,一旦有血栓形成迹象,在应用血管超声和上肢深静脉血管造影明确后,应尽早行抗凝治疗和采取避免血栓脱落措施。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72岁,因右下肺腺癌(cT3N0M1a Ⅳ期)、胸膜转移、肝转移、阻塞性肺炎入院化疗。入院完善检查,双上肢及双下肢行血管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次日行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术,即B超引导下于右上肢近肘部上臂3分之1贵要静脉处置入PICC导管,妥善固定,过程顺利,未见明显出血,右上肢肘横纹上10 cm测上臂臂围27 cm。并于PICC导管放置后第2天开始行第1程化疗,化疗方案为培美曲塞+顺铂+贝伐单抗。3天后化疗给药完成。
化疗结束后第2天,患者突然出现右上肢肿胀,未诉疼痛,查体右上肢水肿明显、皮温略高,右上肢肘横纹上10 cm测上臂臂围31 cm。考虑PICC相关急性上肢静脉血栓形成可能性大,推轮椅去B超室行上肢血管超声检查。B超显示右侧锁骨下静脉、腋静脉、贵要静脉血栓形成。患者返回病房途中突然诉胸闷、气促,随之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立即就近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组织抢救,测脉搏氧饱和度80%、心率106次/min、血压88/40 mm Hg(1 mm Hg=0.133 kPa)、呼吸30次/min,高度怀疑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立即给予多巴胺静脉注射升压,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仪给予氧浓度80%行呼吸支持,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抗凝。后患者神智逐渐转清,血压回升至103/62 mm Hg,脉搏氧饱和度升至92%,心率96次/min,呼吸26次/min。
病情相对平稳后转入我科呼吸ICU继续给予低分子肝素抗凝;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仪吸氧浓度60%,流量30 L/min呼吸支持;去甲肾上腺素升压行循环支持;右上肢制动,绝对卧床,定期测量臂围及患侧皮温变化。患者仍诉胸闷、气促。查血气分析提示:pH7.479,氧分压68.2 mm Hg,二氧化碳分压36.1 mm Hg,氧合指数113.6 mm Hg,动脉血乳酸1.6 mmol/L,查血D-二聚体18.635 mg/L,明显升高。心脏超声提示右心室扩大,肺动脉显示不清,未能测出肺动脉压力。次日,患者自觉症状明显缓解,右侧上臂臂围自31 cm降至28 cm,未吸氧状态下脉搏氧饱和度95%~97%,呼吸22次/min,停用去甲肾上腺素后血压120/75 mm Hg,心率60次/min。复查血气分析:pH7.432,氧分压79.80 mm Hg,二氧化碳分压39.5 mm Hg,氧合指数380 mm Hg,动脉血乳酸0.70 mmol/L。复查血D-二聚体7.496 mg/L,较前明显下降。
患者病情已趋平稳,遂前往CT室行CT肺动脉造影(CT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提示“左肺动脉主干末端、左上、左下肺动脉主干及部分分支、右上肺动脉前段分支内见低密度充盈缺损,考虑肺栓塞可能”(图1)。结合心脏超声右心扩大,以及患者急性起病,以意识丧失、低血压、低氧血症为主要表现,需要使用升压药才能纠正低血压等临床表现,根据2018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颁布的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患者符合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1]。因其右上肢深静脉系统沿PICC导管走行多发血栓形成,如强行拔除导管恐造成致命性肺栓塞,故保留该PICC导管继续维持患者化疗通道。根据该指南[1],继续给予患者低分子肝素抗凝,出院后改用利伐沙班继续抗凝治疗。2个月后复查CTPA显示“与前片示双侧肺动脉低密度充盈缺损,此次未见”(图2)。复查右上肢血管超声:原右上肢深静脉血栓均已消失。血栓脱落加重肺栓塞的风险已经消除,故拔除PICC导管,管端完整,未见血栓。请胸外科为其放置静脉输液岗,继续行抗肿瘤化疗治疗。
该病例没有溶栓主要考虑为以下几点:(1)患者使用了贝伐珠单抗这一抗血管生成药,有发生出血的风险;(2)患者年龄偏大,已经接近溶栓年龄高限;(3)在确诊肺栓塞之前的经验性抗凝治疗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氧合改善,右上肢因血栓引起的肿胀也明显消退。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抗凝治疗对患者相对安全,且患者血栓形成时间短,比较疏松;从临床表现来看,在抗凝治疗的基础上血栓已经开始自溶,再次发生致命性肺栓塞的风险较低,允许密切监测下继续抗凝治疗,如出现病情恶化的情况可随时进行溶栓治疗。后患者症状逐渐好转,故未行溶栓治疗。
该患者在放置PICC之前,曾行双下肢血管超声,未发现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在B超引导下行PICC置放术时,也未经超声发现右上肢静脉系统有血栓形成。此次肺血栓栓塞发生前曾出现明显的右上肢肿胀症状,后B超显示“右侧锁骨下静脉、腋静脉、贵要静脉血栓形成”而双下肢血管超声仍未发现血栓征象。此外,该患者本次入院未行PICC置入术时查D-二聚体正常,而在肺血栓栓塞当日其D-二聚体显著升高。由此可见其肺血栓栓塞的栓子来源应为右上肢深静脉血栓脱落,而右上肢深静脉血栓沿PICC导管走行形成,并在PICC导管置入后出现,故应与PICC导管置入有关,因此该患者应明确诊断为PICC相关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症。
2 讨论
PICC具有安全性强、留置时间长、减少穿刺的痛苦等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化疗,肠外营养,急危重症等治疗过程[2]。一项纳入美国密歇根州48家医院的76 242例住院患者的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放置PICC的患者发生上肢近心端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为2.75/1 000患者日,下肢近心端深静脉血栓发生率1.04/1 000患者日,显著高于没有放置PICC的0.2/1 000患者日和0.44/1 000患者日。但在肺栓塞发生率方面,放置PICC的和非放置PICC分别为0.75/1 000患者日和0.44/1 000患者日,没有显著差异[3]。由此可见,PICC相关肺栓塞的发生率较低,而PICC相关高危肺栓塞就更为少见,查阅近年来文献尚未有相关报道。本例患者发生PICC相关急性高危肺血栓栓塞属于急性高危肺栓塞的一种类型,导致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低氧血症型呼吸衰竭、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才能纠正的低血压循环障碍,属于PICC相关致命性高危肺栓塞,虽然少见,但却极为凶险,临床上应给予高度重视。
本例为肺癌、化疗患者,属于PICC相关深静脉血栓的高风险人群[3-5]。此外,患者在化疗同时应用了抗血管生成药贝伐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正式药品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中明确写明该药存在发生静脉血栓的风险。Howlett等[6]研究也发现在108例肺癌患者中应用贝伐珠单抗治疗,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患者达到了11例(10.2%),统计学分析显示有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风险比为2.39,95%置信区间1.29~4.42,P=0.006)。因此,本例患者同时存在肺癌、化疗、应用PICC以及应用抗血管生成药贝伐珠单抗等多个深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的叠加可能是导致该患者更早和更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甚至肺栓塞的重要原因。患者在放置PICC导管后5天即出现放置导管侧上肢深静脉多发血栓形成和高危肺栓塞,而以往也有报道肿瘤患者PICC相关血栓70%发生在置管后第1周,30%发生在置管后第2周[7]。由此可见,对于恶性肿瘤化疗的患者,放置PICC导管后需要更加密切地监测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尤其在置管后的2周内,如每日策上臂臂围、超声检查有无血栓形成、监测血D-二聚体等,一旦出现上肢肿胀、臂围增加,立即绝对卧床,患肢制动,进行床旁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如有血栓形成应立即进行抗凝治疗。
一项纳入64项研究共计29 503例患者的荟萃研究显示,PICC较中心静脉导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s,CVC)更容易发生上肢深静脉血栓,尤其是在重症患者和肿瘤患者中其上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更高。但PICC并不是引起肺栓塞的高危因素,也没有显著增加肺栓塞的发生率,且没有发生致命性肺栓塞的报道[8]。而另一项纳入75项研究共计10 9292例患者的荟萃研究也显示PICC较CVC更容易出现DVT,但在其中的随机对照研究却显示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9]。另一项关于86例CVC相关上肢深静脉血栓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在纳入的患者中13例发生了肺栓塞,其肺栓塞发病率高达15.1%,其中2例在使用了肝素抗凝治疗后仍死于肺栓塞,病死率2.3%[10]。可见PICC和CVC都是上肢深静脉血栓的高风险因素,但两者之间谁更容易引起血栓尚无定论。但CVC可能较PICC更容易发生致命性高危肺栓塞。我们推测CVC更容易发生致死性肺栓塞的原因是其穿刺和置管位置导致锁骨下静脉、股静脉和髂静脉等近心端粗大的深静脉有形成较大血栓的风险。而本例患者也被证实在锁骨下静脉形成了血栓,这可能是其发生致命性高危肺栓塞的重要原因。今后我们将更加关注PICC相关锁骨下静脉血栓形成与肺栓塞和高危肺栓塞发生的相关性,并做好发现锁骨下静脉血栓后肺栓塞的预防工作。
本例患者发生的事件说明PICC也可以引起致命性高危肺栓塞,虽然少见,但却是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一旦抢救不及时,很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对该类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有必要进行有效预防。但有研究显示预防性抗凝并没有减少PICC相关血栓发生率[9,11]。因此,PICC术后密切监测血栓发生情况显得尤为重要,如上肢臂围监测、血D-二聚体监测等,一旦有血栓形成迹象,在应用血管超声和上肢深静脉血管造影明确后,应尽早行抗凝治疗和采取避免血栓脱落措施。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