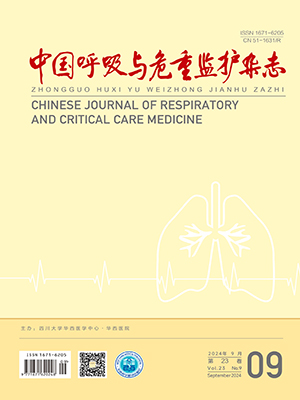引用本文: 任洁, 汤荣, 杨锴, 谢国钢, 丁凤鸣, 张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继发诺卡菌病合并活动性肺结核一例并文献复习.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4, 23(7): 504-508. doi: 10.7507/1671-6205.202401060 复制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继发活动性肺结核常见,但同时合并诺卡菌病罕见[1]。诺卡菌属于革兰阳性需氧放线菌,抗酸染色呈弱阳性,主要感染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其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缺乏特异性,病原学培养增殖速度慢,容易漏诊[2]。此外,诺卡菌导致慢性化脓性炎症可使宿主肺部CD4+ T细胞免疫反应低下,从而干扰活动性肺结核的免疫学诊断结果[3]。本文报告了1例72岁女性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长期反复发热,通过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学二代基因测序发现圣乔治教堂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病例,并总结相关文献。希望临床医师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反复发热患者在鉴别诊断中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诺卡菌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避免漏诊、误诊而延误治疗。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72岁,因“反复咳嗽、咳痰伴发热10个月余”于2023年11月25日入院。患者2023年1月5日因“咳嗽乏力10天”入住当地医院,测体温37.7℃,血常规显示白细胞13.5×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4.3%,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54.43 mg/L,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胸部CT显示两肺多发渗出性改变,肺底散在磨玻璃影,两肺部分支气管轻度扩张,右肺中叶局部支气管狭窄(图1a、b)。随后气管镜检查显示两侧支气管炎性改变。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感染”,予奈玛特韦/利托那韦抗病毒、地塞米松抗炎以及头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和化痰平喘等对症处理,经治疗后患者症状好转出院。出院后患者反复出现发热,发热时体温波动于38~39℃,在当地予静脉头孢类抗生素抗感染治疗1周后体温可降至正常,但2~3周后又出现发热,伴有咳嗽脓痰,上述症状反复发作,持续10个月余。11月22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9℃,在当地医院查白细胞18.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8.7%、CRP 77.3 mg/L,胸部CT提示两肺多发感染伴部分实变,予头孢曲松联合左氧氟沙星抗感染后体温较前下降。11月25日患者到我院门诊就诊,复查血常规白细胞21.2×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3.1%,CRP 74.1 mg/L。为求进一步诊治,拟“发热原因待查”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无明显腹痛、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无明显头痛、晕厥、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无明显皮疹、关节疼痛、口干等结缔组织疾病表现。患者既往否认慢性基础疾病,职业为农民,无烟酒嗜好。
 图1
胸部CT检查像
图1
胸部CT检查像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时,患者胸部CT(2023年1月12日)显示部分支气管轻度扩张,右肺中叶局部支气管狭窄(图a);两肺多发炎症性改变,双侧肺底散在磨玻璃影(图b);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患者出现反复发热10月余,此次入院后患者胸部CT(2023年11月28日)显示双肺部分支气管扩张,可见“树芽征”,右肺上叶可见实变影伴周围渗出,右肺中叶不张(图c),双侧肺底散在斑片渗出灶(图d)。
入院查体:体温37.3℃,脉搏98 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120/85 mm Hg(1 mm Hg=0.133 kPa),神志清,精神萎,全身皮肤未见皮疹,双侧锁骨上未触及肿大淋巴结,肺部听诊双侧肺底可闻及少许湿啰音,心脏及腹部未见异常,双下肢未见水肿。
入院诊断:发热原因待查(特殊病原体肺部感染?)
入院诊治经过:患者入院前长期反复发热伴有中性粒细胞和CRP升高,胸部CT提示渗出性病变,β-内酰胺类抗生素无法有效控制病情,首先考虑肺部特殊病原体感染可能。入院后积极完善感染相关检查,红细胞沉降率100 mm/h;降钙素原正常范围(0.05 ng/mL);呼吸道流感病原体IgM胶体金检测显示呼吸道合胞病毒弱阳性,甲流、乙流、副流感、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腺病毒和柯萨奇病毒B组均为阴性;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血液T-SPOT.TB检测阴性;HIV抗体阴性;血液T/B/NK淋巴细胞计数显示CD3、CD4、CD8、CD19、NK细胞计数均正常;痰真菌涂片未见孢子和菌丝,真菌培养白色酵母菌生长;痰浓缩集菌未找到抗酸杆菌;痰细菌涂片未见可疑细菌,痰微生物培养48 h正常菌群生长;β-D-葡聚糖110 pg/mL。
入院后给予氨苄西林舒巴坦(3 g,1次/8 h)联合莫西沙星(0.4 g,1次/d)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以及化痰、营养支持。由于感染相关检测未有诊断提示意义,故予以复查胸部CT,显示双肺部分支气管扩张,可见“树芽征”,右肺上叶可见实变影伴周围渗出,右肺中叶不张,双侧肺底散在斑片渗出灶(图1c、d),随后行支气管镜检查,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送检。镜下发现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右侧支气管中叶以及双侧支气管下叶基底段开口可见脓性分泌物(图2a),于右侧中叶支气管开口予20 mL生理盐水灌洗6次,混合后送检。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查:黄色,非常浑浊,有核细胞计数8 000×106/L,中性粒细胞85%,肺泡巨噬细胞12%,淋巴细胞2%,嗜酸性粒细胞1%,糖原染色阴性,铁染色查含铁血黄素细胞阴性,特殊染色查耶氏肺孢子菌阴性,真菌、隐球菌涂片检查未查见。肺泡灌洗液细胞因子测定显示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为26.05 pg/mL↑、IL-8为4 589.48 pg/mL↑、IL-1β 为116.83 pg/mL↑、干扰素γ为5.76 pg/mL;肺泡灌洗液T细胞免疫分型显示CD3+CD4+ (辅助/诱导T细胞)0.39%↓、CD3+CD38+(T细胞活化亚群)3.09%↓、CD4+CD28+(辅助T细胞功能亚群)0.39%↓、CD4–CD8– 39.99%(双阴性T细胞)↑。与微生物室沟通,延长痰微生物培养时间,72 h后血琼脂平板上可见淡黄色菌落生长(图2b),经质谱鉴定为圣乔治教堂诺卡菌(MALDI Biotyper微生物质谱快速鉴定系统,Score=1.73,图2c)。灌洗液宏基因组学二代基因测序显示圣乔治诺卡菌(序列数3 951,图2d)和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序列数295,图2e)。
 图2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微生物学检查结果
图2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微生物学检查结果
支气管镜检查(2023年11月30日)显示患者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支气管腔内可见脓性分泌物(图a);肺泡灌洗液微生物培养1周后,血培养皿可见大量淡黄色菌落生长(图b);质谱检测(MALDI Biotyper微生物质谱快速鉴定系统),鉴定为圣乔治教堂诺卡菌(Score =1.73)(图c);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检测显示圣乔治教堂诺卡菌序列数3 951(图d),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序列数295(图e),鉴定置信度99%。
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和微生物学检测结果考虑患者为诺卡菌病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给予出院带药复方磺胺甲恶唑片(0.96 g,4 次/d),同时给予异烟肼(0.3 g,1次/d)、利福平(0.45 g,1次/d)、吡嗪酰胺(0.5 g,3次/d)、乙胺丁醇(0.75 g,1次/d)抗痨治疗。2周后门诊随访,患者咳嗽、咳痰明显减轻,无发热,一般情况良好,复查白细胞7.6×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2.6%,CRP 18.5 mg/L,肝肾功能在正常范围,继续目前抗感染治疗。2个月后再次随访,患者无明显咳嗽、咳痰,状态良好,复查白细胞6.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49.0%,CRP 4.45 mg/L;肝肾功能在正常范围,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7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27 U/L,肌酐71 μmol/L,尿素6.5 mmol/L。
2 讨论
诺卡菌分布广泛,在水、土壤、衰败的植被和动物群中广泛传播,可以附着于灰尘或生物气溶胶而被吸入导致肺部感染,引起全身播散[4]。诺卡菌感染在免疫缺陷患者(包括实体器官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受体、实体肿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以及HIV感染患者)中风险最高,其他风险因素包括全身/吸入皮质类固醇使用、糖尿病、慢性肺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扩张症和囊性纤维化)等[2]。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目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期间或感染后不久出现的诺卡菌病仅有少数病例报道。Stamos等[1]通过对已有的10例病例报告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患者都有易感染诺卡菌的风险因素,且在住院期间接受了糖皮质激素治疗。本病例患者虽然为非免疫抑制宿主,但职业为农民,具有环境高危因素,并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病期间曾使用全身激素治疗,因此属于诺卡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此外,由于长期化脓性感染,肺泡灌洗液T细胞免疫分型显示肺部CD4+辅助T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因此同时具有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高危因素。
诺卡菌病患者的临床表现通常非特异性,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有时还伴有胸痛;临床征象包括白细胞增多和CRP升高[5-6]。在胸部高分辨CT中,肺诺卡菌病最常见的征象是肺结节或肿块,此外胸腔积液、肺部渗出性病灶也可能存在。诺卡菌病诊断需要结合临床和实验室检查[7]。对于不明原因慢性肺部感染患者,需要考虑诺卡菌感染可能性,在呼吸道标本(痰液或肺泡灌洗液)病原学检测中应重点排查诺卡菌。诺卡菌的典型细菌涂片和革兰染色表现为革兰阳性杆菌,排列成细枝细丝状,次级分枝可见菌丝呈90°分枝角,弱抗酸染色阳性。诺卡菌繁殖速度慢,一般需5~7天才可见白色或淡黄色菌落,菌落表面可出现皱褶。细菌培养耗时长,有时需要延长培养时间至2周,甚至需要先用氢氧化钠杀死其他杂菌再进行培养,易延误治疗。PCR或宏基因测序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可实现快速且高效的诊断效率[8]。诺卡菌物种鉴定的金标准是对16S rRNA,hsp65,secA1和sodA中的1个或2个基因进行扩增和测序。准确的物种鉴定有助于明确病原学诊断,提供精准抗感染治疗的靶点[9]。
与诺卡菌病相似,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也常见于免疫损害患者。这两种病原体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差别,均可出现发热、咳嗽、脓痰、体重减轻、乏力和盗汗等,因此在临床实践中经常被误诊[10]。影像学上两者均可出现空洞,伴有坏死和组织破坏,也可伴有胸腔积液和肉芽肿,往往难以鉴别[11]。若既往肺结核治愈遗留肺部结构异常的患者感染诺卡菌,诊断则更加困难,常被误认为结核病复发。诺卡菌采用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方法也可以生长,如果不仔细鉴定,耐药性检查结果和非结核分枝杆菌结果相似,又易误诊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此外,结核合并诺卡菌感染时抗酸染色也可呈阳性,与单纯结核感染时结果相似,易漏诊诺卡菌感染[12]。共同感染的罕见性导致了一种病原体的发现可能会降低其他病原体存在的怀疑,明确诊断必须依靠病原学检测结果。
本病例虽然通过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测序发现大量结核分枝杆菌序列,但外周血T-SPOT.TB检测结果却为阴性,推测可能与患者肺泡灌洗液CD4+ T细胞比例明显降低,影响肺组织感染部位淋巴细胞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免疫反应有关[3]。该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呼吸屏障固有免疫反应功能障碍,随后继发诺卡菌慢性感染使肺组织长期处于化脓性炎症状态,上述感染引起的病理生理改变导致肺组织出现CD4+ T细胞耗竭。一方面使患者肺组织局部免疫功能低下,影响宿主控制潜在或新发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能力,引起结核分枝杆菌从肉芽肿中逃逸并在肺内传播,导致活动性肺结核[13];另一方面也干扰活动性肺结核免疫相关诊断结果,影响外周血释放干扰素γ的结核特异性T淋巴细胞检测,使T-SPOT.TB出现假阴性[14]。因此,对于诺卡菌病患者不应仅根据外周血免疫诊断结果排除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而应重视肺部感染部位的病原学检测结果。
目前诺卡菌感染在血清学方面尚没有发现特异性指标。近年来多例病例报道诺卡菌病患者检出β-D-葡聚糖血清水平升高[15]。虽然β-D-葡聚糖是真菌细胞壁的主要成份,但一些种类的诺卡菌(如星形诺卡菌、皮疽诺卡菌等)细胞壁也可能存在β-D-葡聚糖成份,从而引起交叉反应。此外,采用仅针对诺卡菌而对真菌无作用的抗生素(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治疗后,患者血清中的β-D-葡聚糖出现下降。本例患者β-D-葡聚糖也出现轻度升高(110 pg/mL),因此β-D-葡聚糖升高提示诺卡菌感染可能,但其临床应用价值仍有待于相关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对于免疫功能受损人群,感染诺卡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细胞免疫反应受损。人体免疫系统对诺卡菌的免疫反应始于单核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吞噬大部分细菌并抑制其生长,随后需要活化T淋巴细胞直接接触细菌导致其裂解,防止肺部或全身细菌播散,因此T细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更易感染诺卡菌。目前相关细胞免疫反应尚缺乏风险评估标准,建议在有条件的临床实验室进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包括总T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NK细胞的比例及数量,开展相关风险评估研究。
磺胺类药物是治疗诺卡菌病的一线药物,其中最常用复方磺胺甲噁唑(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TMP-SMX)[16]。TMP-SMX治疗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肝毒性和肾功能不全等[17]。对于抗结核治疗临床常用四联疗法: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这4种药物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发挥杀菌或抑菌作用[18]。药物不良反应包括肝损害、高尿酸血症、周围神经病变等[19]。因此,对于多种病原体合并感染患者用药时应更加谨慎,在联合治疗时注意监测患者血常规及肝肾功能,警惕不良反应发生。
以“新型冠状病毒”“诺卡菌”及“结核”为检索词,通过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进行中文文献检索;同时在PubMed数据库以“COVID-19 AND (Nocardia OR Nocardiosis) AND (TB O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为检索词进行英文文献检索,均暂时未检索到类似本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继发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病例报告。本例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长期反复发热,通过肺泡灌洗液病原学检测发现圣乔治教堂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可知,诺卡菌临床特征无特异性,影像学表现和肺结核相似,易出现误诊和漏诊。因此,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反复发热患者,应注重基于分子生物学的病原微生物检测,考虑是否存在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避免漏诊、误诊而延误治疗。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继发活动性肺结核常见,但同时合并诺卡菌病罕见[1]。诺卡菌属于革兰阳性需氧放线菌,抗酸染色呈弱阳性,主要感染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其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缺乏特异性,病原学培养增殖速度慢,容易漏诊[2]。此外,诺卡菌导致慢性化脓性炎症可使宿主肺部CD4+ T细胞免疫反应低下,从而干扰活动性肺结核的免疫学诊断结果[3]。本文报告了1例72岁女性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长期反复发热,通过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学二代基因测序发现圣乔治教堂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病例,并总结相关文献。希望临床医师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反复发热患者在鉴别诊断中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诺卡菌病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避免漏诊、误诊而延误治疗。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72岁,因“反复咳嗽、咳痰伴发热10个月余”于2023年11月25日入院。患者2023年1月5日因“咳嗽乏力10天”入住当地医院,测体温37.7℃,血常规显示白细胞13.5×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4.3%,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54.43 mg/L,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胸部CT显示两肺多发渗出性改变,肺底散在磨玻璃影,两肺部分支气管轻度扩张,右肺中叶局部支气管狭窄(图1a、b)。随后气管镜检查显示两侧支气管炎性改变。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感染”,予奈玛特韦/利托那韦抗病毒、地塞米松抗炎以及头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和化痰平喘等对症处理,经治疗后患者症状好转出院。出院后患者反复出现发热,发热时体温波动于38~39℃,在当地予静脉头孢类抗生素抗感染治疗1周后体温可降至正常,但2~3周后又出现发热,伴有咳嗽脓痰,上述症状反复发作,持续10个月余。11月22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9℃,在当地医院查白细胞18.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8.7%、CRP 77.3 mg/L,胸部CT提示两肺多发感染伴部分实变,予头孢曲松联合左氧氟沙星抗感染后体温较前下降。11月25日患者到我院门诊就诊,复查血常规白细胞21.2×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3.1%,CRP 74.1 mg/L。为求进一步诊治,拟“发热原因待查”收住入院。病程中患者无明显腹痛、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无明显头痛、晕厥、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无明显皮疹、关节疼痛、口干等结缔组织疾病表现。患者既往否认慢性基础疾病,职业为农民,无烟酒嗜好。
 图1
胸部CT检查像
图1
胸部CT检查像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时,患者胸部CT(2023年1月12日)显示部分支气管轻度扩张,右肺中叶局部支气管狭窄(图a);两肺多发炎症性改变,双侧肺底散在磨玻璃影(图b);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患者出现反复发热10月余,此次入院后患者胸部CT(2023年11月28日)显示双肺部分支气管扩张,可见“树芽征”,右肺上叶可见实变影伴周围渗出,右肺中叶不张(图c),双侧肺底散在斑片渗出灶(图d)。
入院查体:体温37.3℃,脉搏98 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120/85 mm Hg(1 mm Hg=0.133 kPa),神志清,精神萎,全身皮肤未见皮疹,双侧锁骨上未触及肿大淋巴结,肺部听诊双侧肺底可闻及少许湿啰音,心脏及腹部未见异常,双下肢未见水肿。
入院诊断:发热原因待查(特殊病原体肺部感染?)
入院诊治经过:患者入院前长期反复发热伴有中性粒细胞和CRP升高,胸部CT提示渗出性病变,β-内酰胺类抗生素无法有效控制病情,首先考虑肺部特殊病原体感染可能。入院后积极完善感染相关检查,红细胞沉降率100 mm/h;降钙素原正常范围(0.05 ng/mL);呼吸道流感病原体IgM胶体金检测显示呼吸道合胞病毒弱阳性,甲流、乙流、副流感、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腺病毒和柯萨奇病毒B组均为阴性;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血液T-SPOT.TB检测阴性;HIV抗体阴性;血液T/B/NK淋巴细胞计数显示CD3、CD4、CD8、CD19、NK细胞计数均正常;痰真菌涂片未见孢子和菌丝,真菌培养白色酵母菌生长;痰浓缩集菌未找到抗酸杆菌;痰细菌涂片未见可疑细菌,痰微生物培养48 h正常菌群生长;β-D-葡聚糖110 pg/mL。
入院后给予氨苄西林舒巴坦(3 g,1次/8 h)联合莫西沙星(0.4 g,1次/d)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以及化痰、营养支持。由于感染相关检测未有诊断提示意义,故予以复查胸部CT,显示双肺部分支气管扩张,可见“树芽征”,右肺上叶可见实变影伴周围渗出,右肺中叶不张,双侧肺底散在斑片渗出灶(图1c、d),随后行支气管镜检查,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送检。镜下发现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右侧支气管中叶以及双侧支气管下叶基底段开口可见脓性分泌物(图2a),于右侧中叶支气管开口予20 mL生理盐水灌洗6次,混合后送检。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查:黄色,非常浑浊,有核细胞计数8 000×106/L,中性粒细胞85%,肺泡巨噬细胞12%,淋巴细胞2%,嗜酸性粒细胞1%,糖原染色阴性,铁染色查含铁血黄素细胞阴性,特殊染色查耶氏肺孢子菌阴性,真菌、隐球菌涂片检查未查见。肺泡灌洗液细胞因子测定显示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为26.05 pg/mL↑、IL-8为4 589.48 pg/mL↑、IL-1β 为116.83 pg/mL↑、干扰素γ为5.76 pg/mL;肺泡灌洗液T细胞免疫分型显示CD3+CD4+ (辅助/诱导T细胞)0.39%↓、CD3+CD38+(T细胞活化亚群)3.09%↓、CD4+CD28+(辅助T细胞功能亚群)0.39%↓、CD4–CD8– 39.99%(双阴性T细胞)↑。与微生物室沟通,延长痰微生物培养时间,72 h后血琼脂平板上可见淡黄色菌落生长(图2b),经质谱鉴定为圣乔治教堂诺卡菌(MALDI Biotyper微生物质谱快速鉴定系统,Score=1.73,图2c)。灌洗液宏基因组学二代基因测序显示圣乔治诺卡菌(序列数3 951,图2d)和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序列数295,图2e)。
 图2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微生物学检查结果
图2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微生物学检查结果
支气管镜检查(2023年11月30日)显示患者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支气管腔内可见脓性分泌物(图a);肺泡灌洗液微生物培养1周后,血培养皿可见大量淡黄色菌落生长(图b);质谱检测(MALDI Biotyper微生物质谱快速鉴定系统),鉴定为圣乔治教堂诺卡菌(Score =1.73)(图c);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检测显示圣乔治教堂诺卡菌序列数3 951(图d),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序列数295(图e),鉴定置信度99%。
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和微生物学检测结果考虑患者为诺卡菌病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给予出院带药复方磺胺甲恶唑片(0.96 g,4 次/d),同时给予异烟肼(0.3 g,1次/d)、利福平(0.45 g,1次/d)、吡嗪酰胺(0.5 g,3次/d)、乙胺丁醇(0.75 g,1次/d)抗痨治疗。2周后门诊随访,患者咳嗽、咳痰明显减轻,无发热,一般情况良好,复查白细胞7.6×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2.6%,CRP 18.5 mg/L,肝肾功能在正常范围,继续目前抗感染治疗。2个月后再次随访,患者无明显咳嗽、咳痰,状态良好,复查白细胞6.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49.0%,CRP 4.45 mg/L;肝肾功能在正常范围,丙氨酸氨基转移酶17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27 U/L,肌酐71 μmol/L,尿素6.5 mmol/L。
2 讨论
诺卡菌分布广泛,在水、土壤、衰败的植被和动物群中广泛传播,可以附着于灰尘或生物气溶胶而被吸入导致肺部感染,引起全身播散[4]。诺卡菌感染在免疫缺陷患者(包括实体器官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受体、实体肿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以及HIV感染患者)中风险最高,其他风险因素包括全身/吸入皮质类固醇使用、糖尿病、慢性肺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扩张症和囊性纤维化)等[2]。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目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期间或感染后不久出现的诺卡菌病仅有少数病例报道。Stamos等[1]通过对已有的10例病例报告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患者都有易感染诺卡菌的风险因素,且在住院期间接受了糖皮质激素治疗。本病例患者虽然为非免疫抑制宿主,但职业为农民,具有环境高危因素,并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病期间曾使用全身激素治疗,因此属于诺卡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此外,由于长期化脓性感染,肺泡灌洗液T细胞免疫分型显示肺部CD4+辅助T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因此同时具有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高危因素。
诺卡菌病患者的临床表现通常非特异性,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有时还伴有胸痛;临床征象包括白细胞增多和CRP升高[5-6]。在胸部高分辨CT中,肺诺卡菌病最常见的征象是肺结节或肿块,此外胸腔积液、肺部渗出性病灶也可能存在。诺卡菌病诊断需要结合临床和实验室检查[7]。对于不明原因慢性肺部感染患者,需要考虑诺卡菌感染可能性,在呼吸道标本(痰液或肺泡灌洗液)病原学检测中应重点排查诺卡菌。诺卡菌的典型细菌涂片和革兰染色表现为革兰阳性杆菌,排列成细枝细丝状,次级分枝可见菌丝呈90°分枝角,弱抗酸染色阳性。诺卡菌繁殖速度慢,一般需5~7天才可见白色或淡黄色菌落,菌落表面可出现皱褶。细菌培养耗时长,有时需要延长培养时间至2周,甚至需要先用氢氧化钠杀死其他杂菌再进行培养,易延误治疗。PCR或宏基因测序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可实现快速且高效的诊断效率[8]。诺卡菌物种鉴定的金标准是对16S rRNA,hsp65,secA1和sodA中的1个或2个基因进行扩增和测序。准确的物种鉴定有助于明确病原学诊断,提供精准抗感染治疗的靶点[9]。
与诺卡菌病相似,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也常见于免疫损害患者。这两种病原体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差别,均可出现发热、咳嗽、脓痰、体重减轻、乏力和盗汗等,因此在临床实践中经常被误诊[10]。影像学上两者均可出现空洞,伴有坏死和组织破坏,也可伴有胸腔积液和肉芽肿,往往难以鉴别[11]。若既往肺结核治愈遗留肺部结构异常的患者感染诺卡菌,诊断则更加困难,常被误认为结核病复发。诺卡菌采用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方法也可以生长,如果不仔细鉴定,耐药性检查结果和非结核分枝杆菌结果相似,又易误诊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此外,结核合并诺卡菌感染时抗酸染色也可呈阳性,与单纯结核感染时结果相似,易漏诊诺卡菌感染[12]。共同感染的罕见性导致了一种病原体的发现可能会降低其他病原体存在的怀疑,明确诊断必须依靠病原学检测结果。
本病例虽然通过肺泡灌洗液宏基因组测序发现大量结核分枝杆菌序列,但外周血T-SPOT.TB检测结果却为阴性,推测可能与患者肺泡灌洗液CD4+ T细胞比例明显降低,影响肺组织感染部位淋巴细胞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免疫反应有关[3]。该患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呼吸屏障固有免疫反应功能障碍,随后继发诺卡菌慢性感染使肺组织长期处于化脓性炎症状态,上述感染引起的病理生理改变导致肺组织出现CD4+ T细胞耗竭。一方面使患者肺组织局部免疫功能低下,影响宿主控制潜在或新发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能力,引起结核分枝杆菌从肉芽肿中逃逸并在肺内传播,导致活动性肺结核[13];另一方面也干扰活动性肺结核免疫相关诊断结果,影响外周血释放干扰素γ的结核特异性T淋巴细胞检测,使T-SPOT.TB出现假阴性[14]。因此,对于诺卡菌病患者不应仅根据外周血免疫诊断结果排除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而应重视肺部感染部位的病原学检测结果。
目前诺卡菌感染在血清学方面尚没有发现特异性指标。近年来多例病例报道诺卡菌病患者检出β-D-葡聚糖血清水平升高[15]。虽然β-D-葡聚糖是真菌细胞壁的主要成份,但一些种类的诺卡菌(如星形诺卡菌、皮疽诺卡菌等)细胞壁也可能存在β-D-葡聚糖成份,从而引起交叉反应。此外,采用仅针对诺卡菌而对真菌无作用的抗生素(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治疗后,患者血清中的β-D-葡聚糖出现下降。本例患者β-D-葡聚糖也出现轻度升高(110 pg/mL),因此β-D-葡聚糖升高提示诺卡菌感染可能,但其临床应用价值仍有待于相关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对于免疫功能受损人群,感染诺卡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细胞免疫反应受损。人体免疫系统对诺卡菌的免疫反应始于单核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吞噬大部分细菌并抑制其生长,随后需要活化T淋巴细胞直接接触细菌导致其裂解,防止肺部或全身细菌播散,因此T细胞免疫功能受损患者更易感染诺卡菌。目前相关细胞免疫反应尚缺乏风险评估标准,建议在有条件的临床实验室进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包括总T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NK细胞的比例及数量,开展相关风险评估研究。
磺胺类药物是治疗诺卡菌病的一线药物,其中最常用复方磺胺甲噁唑(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TMP-SMX)[16]。TMP-SMX治疗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肝毒性和肾功能不全等[17]。对于抗结核治疗临床常用四联疗法: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这4种药物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发挥杀菌或抑菌作用[18]。药物不良反应包括肝损害、高尿酸血症、周围神经病变等[19]。因此,对于多种病原体合并感染患者用药时应更加谨慎,在联合治疗时注意监测患者血常规及肝肾功能,警惕不良反应发生。
以“新型冠状病毒”“诺卡菌”及“结核”为检索词,通过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进行中文文献检索;同时在PubMed数据库以“COVID-19 AND (Nocardia OR Nocardiosis) AND (TB O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为检索词进行英文文献检索,均暂时未检索到类似本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继发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病例报告。本例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长期反复发热,通过肺泡灌洗液病原学检测发现圣乔治教堂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可知,诺卡菌临床特征无特异性,影像学表现和肺结核相似,易出现误诊和漏诊。因此,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反复发热患者,应注重基于分子生物学的病原微生物检测,考虑是否存在诺卡菌合并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避免漏诊、误诊而延误治疗。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