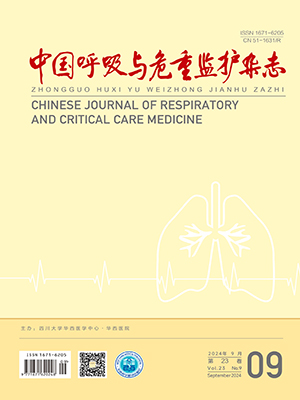引用本文: 袁宾彬, 徐颖, 王倩, 陈丽秋, 梁培, 顾勤. 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治疗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肺炎的临床研究.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4, 23(6): 390-394. doi: 10.7507/1671-6205.202401062 复制
随着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CRO)感染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加[1]。患者发生CRO感染后,可供治疗选择的抗菌药物极少,病死率显著增高[2]。对于CRO感染,目前多个专家共识及指南推荐以多黏菌素为基础的联合用药治疗[3-8]。在应对仅对多黏菌素敏感的革兰阴性菌引起的肺部感染或对全身治疗无反应的患者时,推荐雾化吸入多黏菌素联合静脉滴注治疗[2-5,7]。然而,雾化使用多黏菌素B仍属于超说明书用药,实际相关临床研究较少,临床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缺乏足够认知。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多黏菌素B单纯静脉滴注和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治疗CRO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的方法,收集2020年9月—2023年6月南京鼓楼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使用多黏菌素B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肺炎诊断标准[9];(3)痰培养或肺泡灌洗液培养检出CRO,对多黏菌素敏感;(4)既往未使用过多黏菌素类药物治疗。排除标准:(1)多黏菌素B用药时间≤3 d;(2)妊娠期、哺乳期患者;(3)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患者;(4)恶性肿瘤患者;(5)濒死状态者。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已经南京鼓楼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2021-466-02),所有治疗和监测已得到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患者分组及多黏菌素B用法用量
所有入组患者采用硫酸多黏菌素B(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1022631,规格为50万单位)治疗,静脉滴注初次负荷剂量100万单位,随后每次50万单位,q12h;联合组患者除给予上述静脉给药方案外,同时给予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雾化吸入,每次25万单位,q12 h。使用多黏菌素B雾化前20 min均先使用左旋沙丁胺醇雾化,且多黏菌素B均使用震动筛孔雾化器进行喷射雾化。
根据多黏菌素B治疗方案的不同,将接受多黏菌素B单纯静脉滴注治疗的患者纳入A组,将接受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治疗的患者纳入B组。
1.2.2 观察指标及观察终点
(1)一般情况: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基础疾病以及用药前各项实验室指标基线水平等;(2)主要结果:治疗前后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细胞等感染指标水平,30天全因死亡率;(3)次要结果:细菌清除率、治疗有效率和药物相关不良事件(主要是急性肾损伤)发生率。A组观察终点为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结束,B组观察终点为多黏菌素B静滴及雾化总疗程结束。
1.2.3 疗效判别标准
(1)治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2)改善: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有改善;(3)无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无明显改善,甚至病情加重或改用其他治疗方案,总有效例数=治愈例数+有效例数,总治疗有效率=总有效例数/总例数×100%[10];(4)30天全因死亡率:定义为治疗结束后30天内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
1.2.4 细菌清除评价标准
(1)清除:连续3次细菌培养结果显示为阴性;(2)替换:连续3次细菌培养结果显示为其他细菌生长,且原病原菌消失;(3)未清除:细菌培养结果仍显示为原病原菌生长。总细菌清除例数=清除例数 + 替换例数,总细菌清除率=总细菌清除例数/总例数×100%[10]。
细菌培养敏感性试验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根据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和欧洲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的建议,多黏菌素的敏感性参数被认为是敏感(最小抑菌浓度≤2 mg/L)和耐药(最小抑菌浓度>2 mg/L)[11-12]。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组内比较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共收集使用多黏菌素B治疗患者临床资料180例,其中CRO肺炎患者98例,排除用药不足3天者13例,最终入组85例患者,其中A组50例,B组35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两组患者病原学培养结果显示,A组鲍曼不动杆菌38例,肺炎克雷伯菌16例,铜绿假单胞菌4例,肠杆菌属2例;B组鲍曼不动杆菌27例,肺炎克雷伯菌10例,铜绿假单胞菌5例,肠杆菌属2例。两组病原学培养结果比较如表1所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4),表明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基线均衡。
2.2 多黏菌素B用药及联合其他抗菌药物用药情况
A组患者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为(11.55±5.89)d,B组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为(12.16±6.63)d,雾化吸入疗程为(12.97±5.32)d。两组患者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96)。由表1所见,两组患者主要联合用药为替加环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且两组间联合用药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4)。
2.3 临床疗效分析
2.3.1 用药前后感染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用药前各项感染指标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A组用药后血清PCT、CRP水平较用药前明显降低(P<0.05);B组用药后血清PCT、CRP较用药前也明显降低(P<0.05),且B组用药后PCT水平明显低于A组用药后PCT水平(P=0.029)。两组患者用药前后白细胞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2.3.2 治疗有效率、细菌清除率以及30天全因死亡率比较
A组治疗有效率62.0%(31/50),B组治疗有效率82.9%(29/35);A组细菌清除率4.0%(2/50),B组细菌清除率34.3%(12/35)。B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细菌清除率均显著高于A组患者(均P<0.05)。A组患者用药结束后30天全因死亡率36.0%(18/50),B组患者用药结束后30天全因死亡率31.4%(11/35),两组患者30天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4)。结果见表3。
2.3.3 治疗期间急性肾损伤发生率
A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18%(9/50),B组患者急性肾损伤发生率14.3%(5/35),两组患者用药期间急性肾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50)。结果见表3。
3 讨论
多黏菌素B是一种多肽类抗生素,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革兰阴性杆菌的治疗,但由于其较高的肾毒性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被弃用[13]。近年来,随着细菌耐药性的增加,尤其是CRO的增多,给抗菌药的选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多黏菌素B成为了治疗CRO的最后一道防线之一[14]。重症患者普遍机体免疫力低下、基础疾病多,大量使用各种广谱抗菌药物,各种侵入性操作(如气管插管、吸痰、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等)频繁,导致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医院获得性肺炎感染风险远高于普通病房患者。尤其是CRO等细菌,尽管做了积极的抗菌治疗,但是病原菌可逃避先天性肺防御,极易在肺泡上皮衬液存活,在治疗CRO肺炎患者时,常常难以达到理想临床疗效且易导致多黏菌素耐药菌的出现。所以在治疗CRO重症肺炎患者时,上皮细胞衬液中药物浓度往往更能反映抗感染效果。全身给药时渗透到肺泡上皮衬液的药物有限,肺泡上皮衬液中药物浓度低[15],难以达到理想的抗感染效果。而辅助雾化吸入可以在显著提高多黏菌素肺组织浓度的同时不增加药物全身暴露水平,进而提高抗感染疗效,同时不增加全身不良反应[16-17]。雾化吸入可使多黏菌素B以气雾剂的形式喷射进入气道,可达到快速抗炎,迅速降低血清感染因子的作用[18]。
3.1 有效性
Hasan等[19]研究发现,在治疗重症肺炎克雷伯菌肺炎患者时,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与单纯静脉滴注相比,具有较高的细菌清除率、更短的平均拔管时间和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周丽丽等[20]研究显示,在治疗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肺炎时,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与单纯静脉滴注相比,在降低血清PCT、细菌清除、缩短体温复常时间等方面更有优势。Lin等[21]研究结果也显示雾化吸入联合静脉滴注多黏菌素B可提高细菌清除率,降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一项Meta分析共纳入了13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雾化吸入多黏菌素联合常规治疗能显著提高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临床有效率和微生物清除率[22]。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在治疗CRO重症肺炎患者时,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治疗与单纯静脉滴注治疗相比,有更高的细菌清除率和有效率,且更有助于降低血清PCT水平。但杨依磊等[23]研究显示,对于机械通气重症肺炎患者,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较单独静脉滴注在病死率、临床有效率和细菌清除率都并未显示出更加优越的有效性,在安全性方面反而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显著提高[23],这可能是纳入人群的差异所导致。
3.2 安全性
(1)肾毒性:根据既往研究报道,肾毒性是多黏菌素B最常见的不良反应,通常表现为肌酐清除率降低、血尿素氮浓度升高和少尿等[13]。不同文献报道多黏菌素B肾毒性发生率差异较大,其发生率在12.7%~60%不等[24-27],可能是患者群体选择与肾毒性诊断标准不同所导致。本研究综合评估了患者多黏菌素B药物相关性急性肾损伤,结果显示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与单纯静脉滴注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使用多黏菌素B时,在静脉滴注的基础上联合雾化吸入并不会增加肾毒性的发生风险。(2)气道不良反应:多黏菌素B雾化吸入的常见不良反应有咳嗽、支气管痉挛等。Pereira等[28]发现19例吸入硫酸多黏菌素B的患者中有4例发生咳嗽或支气管痉挛,药物减量后不良反应消失。杨依磊等[23]研究也显示,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较单独静脉滴注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在使用多黏菌素B雾化治疗之前事先使用左旋沙丁胺醇雾化可极大程度上避免相关气道不良反应。(3)皮肤色素沉着:静脉应用多黏菌素B可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多见于颈面部,其具体机制不明,可能与炎症过程中朗格汉斯细胞增生、真皮白细胞介素6过度表达、组胺释放、黑色素细胞活化有关[29]。色素沉着不影响治疗效果,大多数患者停药后3~6个月可自行恢复。本研究患者群体为重症患者,主要评估临床疗效,因此未统计色素沉着发生率。(4)神经毒性:多黏菌素B神经毒性主要表现为头晕及共济失调、面部潮红、嗜睡、外周感觉异常、胸痛等[6],但由于重症患者大多处于镇痛镇静状态,难以评估。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对于患者的选择及不同用药方案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且患者例数偏少,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研究与验证;(3)未监测收集患者血药浓度,无法分析临床疗效及各项指标是否与血药浓度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分析比较单纯静脉滴注和静脉联合雾化吸入治疗CRO肺炎的效果,发现治疗CRO肺炎患者时,在使用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的基础上联合雾化吸入治疗方案优于单纯静脉滴注治疗,且不增加肾毒性发生的风险。在权衡获益与风险后,推荐危重症患者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治疗CRO肺炎。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随着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CRO)感染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加[1]。患者发生CRO感染后,可供治疗选择的抗菌药物极少,病死率显著增高[2]。对于CRO感染,目前多个专家共识及指南推荐以多黏菌素为基础的联合用药治疗[3-8]。在应对仅对多黏菌素敏感的革兰阴性菌引起的肺部感染或对全身治疗无反应的患者时,推荐雾化吸入多黏菌素联合静脉滴注治疗[2-5,7]。然而,雾化使用多黏菌素B仍属于超说明书用药,实际相关临床研究较少,临床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缺乏足够认知。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多黏菌素B单纯静脉滴注和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治疗CRO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的方法,收集2020年9月—2023年6月南京鼓楼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使用多黏菌素B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肺炎诊断标准[9];(3)痰培养或肺泡灌洗液培养检出CRO,对多黏菌素敏感;(4)既往未使用过多黏菌素类药物治疗。排除标准:(1)多黏菌素B用药时间≤3 d;(2)妊娠期、哺乳期患者;(3)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患者;(4)恶性肿瘤患者;(5)濒死状态者。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已经南京鼓楼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2021-466-02),所有治疗和监测已得到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患者分组及多黏菌素B用法用量
所有入组患者采用硫酸多黏菌素B(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1022631,规格为50万单位)治疗,静脉滴注初次负荷剂量100万单位,随后每次50万单位,q12h;联合组患者除给予上述静脉给药方案外,同时给予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雾化吸入,每次25万单位,q12 h。使用多黏菌素B雾化前20 min均先使用左旋沙丁胺醇雾化,且多黏菌素B均使用震动筛孔雾化器进行喷射雾化。
根据多黏菌素B治疗方案的不同,将接受多黏菌素B单纯静脉滴注治疗的患者纳入A组,将接受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治疗的患者纳入B组。
1.2.2 观察指标及观察终点
(1)一般情况: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基础疾病以及用药前各项实验室指标基线水平等;(2)主要结果:治疗前后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细胞等感染指标水平,30天全因死亡率;(3)次要结果:细菌清除率、治疗有效率和药物相关不良事件(主要是急性肾损伤)发生率。A组观察终点为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结束,B组观察终点为多黏菌素B静滴及雾化总疗程结束。
1.2.3 疗效判别标准
(1)治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2)改善: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有改善;(3)无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病原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无明显改善,甚至病情加重或改用其他治疗方案,总有效例数=治愈例数+有效例数,总治疗有效率=总有效例数/总例数×100%[10];(4)30天全因死亡率:定义为治疗结束后30天内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
1.2.4 细菌清除评价标准
(1)清除:连续3次细菌培养结果显示为阴性;(2)替换:连续3次细菌培养结果显示为其他细菌生长,且原病原菌消失;(3)未清除:细菌培养结果仍显示为原病原菌生长。总细菌清除例数=清除例数 + 替换例数,总细菌清除率=总细菌清除例数/总例数×100%[10]。
细菌培养敏感性试验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根据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和欧洲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的建议,多黏菌素的敏感性参数被认为是敏感(最小抑菌浓度≤2 mg/L)和耐药(最小抑菌浓度>2 mg/L)[11-12]。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组内比较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共收集使用多黏菌素B治疗患者临床资料180例,其中CRO肺炎患者98例,排除用药不足3天者13例,最终入组85例患者,其中A组50例,B组35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1)。两组患者病原学培养结果显示,A组鲍曼不动杆菌38例,肺炎克雷伯菌16例,铜绿假单胞菌4例,肠杆菌属2例;B组鲍曼不动杆菌27例,肺炎克雷伯菌10例,铜绿假单胞菌5例,肠杆菌属2例。两组病原学培养结果比较如表1所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4),表明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基线均衡。
2.2 多黏菌素B用药及联合其他抗菌药物用药情况
A组患者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为(11.55±5.89)d,B组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为(12.16±6.63)d,雾化吸入疗程为(12.97±5.32)d。两组患者多黏菌素B静滴疗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96)。由表1所见,两组患者主要联合用药为替加环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且两组间联合用药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4)。
2.3 临床疗效分析
2.3.1 用药前后感染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用药前各项感染指标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A组用药后血清PCT、CRP水平较用药前明显降低(P<0.05);B组用药后血清PCT、CRP较用药前也明显降低(P<0.05),且B组用药后PCT水平明显低于A组用药后PCT水平(P=0.029)。两组患者用药前后白细胞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2.3.2 治疗有效率、细菌清除率以及30天全因死亡率比较
A组治疗有效率62.0%(31/50),B组治疗有效率82.9%(29/35);A组细菌清除率4.0%(2/50),B组细菌清除率34.3%(12/35)。B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细菌清除率均显著高于A组患者(均P<0.05)。A组患者用药结束后30天全因死亡率36.0%(18/50),B组患者用药结束后30天全因死亡率31.4%(11/35),两组患者30天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4)。结果见表3。
2.3.3 治疗期间急性肾损伤发生率
A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18%(9/50),B组患者急性肾损伤发生率14.3%(5/35),两组患者用药期间急性肾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50)。结果见表3。
3 讨论
多黏菌素B是一种多肽类抗生素,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革兰阴性杆菌的治疗,但由于其较高的肾毒性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被弃用[13]。近年来,随着细菌耐药性的增加,尤其是CRO的增多,给抗菌药的选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多黏菌素B成为了治疗CRO的最后一道防线之一[14]。重症患者普遍机体免疫力低下、基础疾病多,大量使用各种广谱抗菌药物,各种侵入性操作(如气管插管、吸痰、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等)频繁,导致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医院获得性肺炎感染风险远高于普通病房患者。尤其是CRO等细菌,尽管做了积极的抗菌治疗,但是病原菌可逃避先天性肺防御,极易在肺泡上皮衬液存活,在治疗CRO肺炎患者时,常常难以达到理想临床疗效且易导致多黏菌素耐药菌的出现。所以在治疗CRO重症肺炎患者时,上皮细胞衬液中药物浓度往往更能反映抗感染效果。全身给药时渗透到肺泡上皮衬液的药物有限,肺泡上皮衬液中药物浓度低[15],难以达到理想的抗感染效果。而辅助雾化吸入可以在显著提高多黏菌素肺组织浓度的同时不增加药物全身暴露水平,进而提高抗感染疗效,同时不增加全身不良反应[16-17]。雾化吸入可使多黏菌素B以气雾剂的形式喷射进入气道,可达到快速抗炎,迅速降低血清感染因子的作用[18]。
3.1 有效性
Hasan等[19]研究发现,在治疗重症肺炎克雷伯菌肺炎患者时,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与单纯静脉滴注相比,具有较高的细菌清除率、更短的平均拔管时间和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周丽丽等[20]研究显示,在治疗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肺炎时,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与单纯静脉滴注相比,在降低血清PCT、细菌清除、缩短体温复常时间等方面更有优势。Lin等[21]研究结果也显示雾化吸入联合静脉滴注多黏菌素B可提高细菌清除率,降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一项Meta分析共纳入了13项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雾化吸入多黏菌素联合常规治疗能显著提高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临床有效率和微生物清除率[22]。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在治疗CRO重症肺炎患者时,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治疗与单纯静脉滴注治疗相比,有更高的细菌清除率和有效率,且更有助于降低血清PCT水平。但杨依磊等[23]研究显示,对于机械通气重症肺炎患者,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较单独静脉滴注在病死率、临床有效率和细菌清除率都并未显示出更加优越的有效性,在安全性方面反而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显著提高[23],这可能是纳入人群的差异所导致。
3.2 安全性
(1)肾毒性:根据既往研究报道,肾毒性是多黏菌素B最常见的不良反应,通常表现为肌酐清除率降低、血尿素氮浓度升高和少尿等[13]。不同文献报道多黏菌素B肾毒性发生率差异较大,其发生率在12.7%~60%不等[24-27],可能是患者群体选择与肾毒性诊断标准不同所导致。本研究综合评估了患者多黏菌素B药物相关性急性肾损伤,结果显示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与单纯静脉滴注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使用多黏菌素B时,在静脉滴注的基础上联合雾化吸入并不会增加肾毒性的发生风险。(2)气道不良反应:多黏菌素B雾化吸入的常见不良反应有咳嗽、支气管痉挛等。Pereira等[28]发现19例吸入硫酸多黏菌素B的患者中有4例发生咳嗽或支气管痉挛,药物减量后不良反应消失。杨依磊等[23]研究也显示,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较单独静脉滴注支气管痉挛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在使用多黏菌素B雾化治疗之前事先使用左旋沙丁胺醇雾化可极大程度上避免相关气道不良反应。(3)皮肤色素沉着:静脉应用多黏菌素B可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多见于颈面部,其具体机制不明,可能与炎症过程中朗格汉斯细胞增生、真皮白细胞介素6过度表达、组胺释放、黑色素细胞活化有关[29]。色素沉着不影响治疗效果,大多数患者停药后3~6个月可自行恢复。本研究患者群体为重症患者,主要评估临床疗效,因此未统计色素沉着发生率。(4)神经毒性:多黏菌素B神经毒性主要表现为头晕及共济失调、面部潮红、嗜睡、外周感觉异常、胸痛等[6],但由于重症患者大多处于镇痛镇静状态,难以评估。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对于患者的选择及不同用药方案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且患者例数偏少,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研究与验证;(3)未监测收集患者血药浓度,无法分析临床疗效及各项指标是否与血药浓度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分析比较单纯静脉滴注和静脉联合雾化吸入治疗CRO肺炎的效果,发现治疗CRO肺炎患者时,在使用多黏菌素B静脉滴注的基础上联合雾化吸入治疗方案优于单纯静脉滴注治疗,且不增加肾毒性发生的风险。在权衡获益与风险后,推荐危重症患者静脉滴注联合雾化吸入多黏菌素B治疗CRO肺炎。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